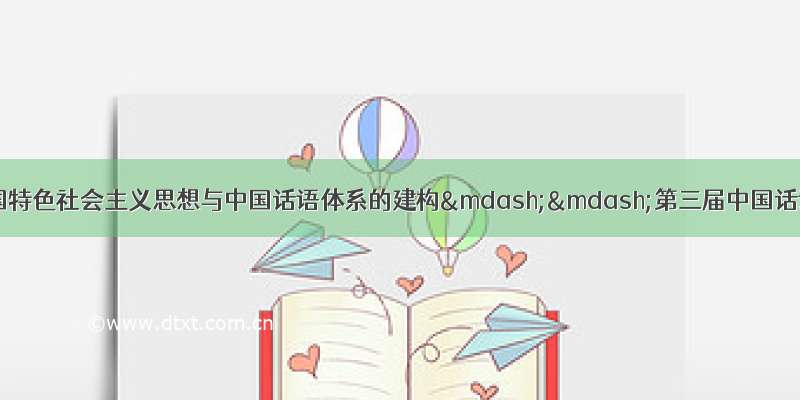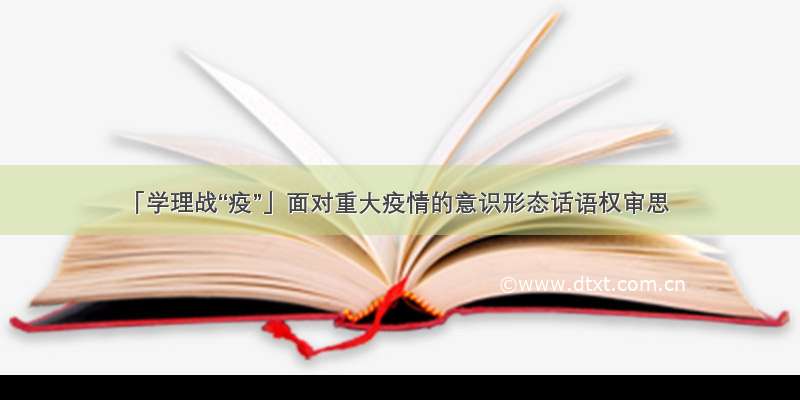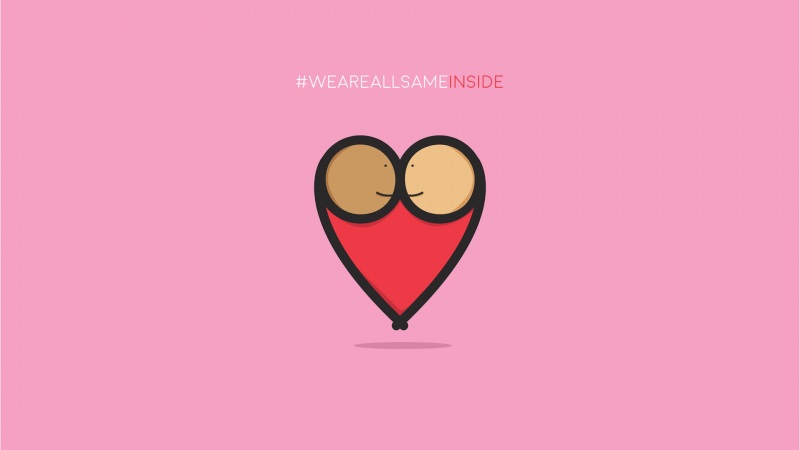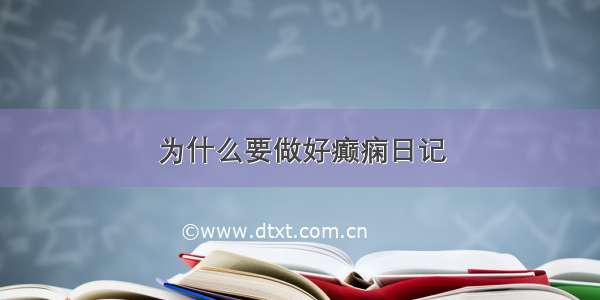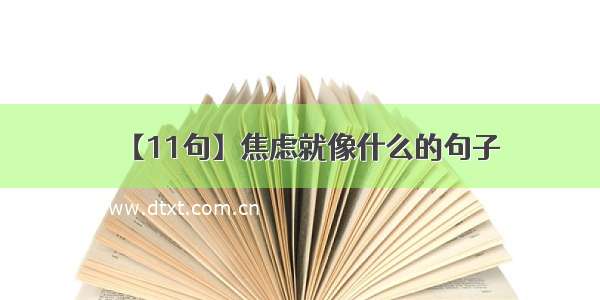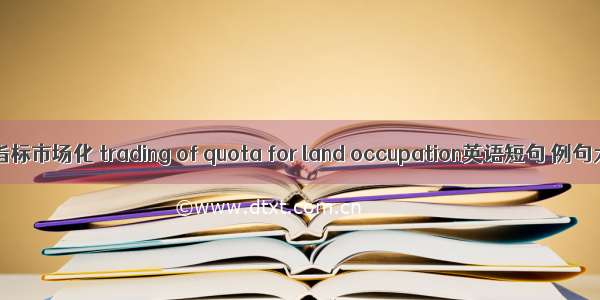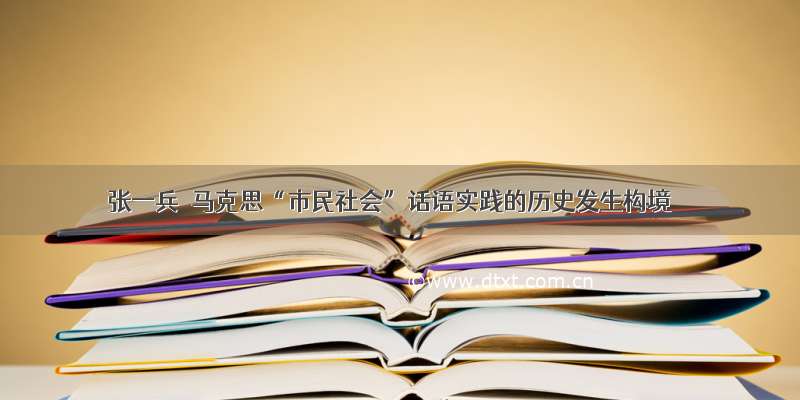
「来源: |新大众哲学 ID:xindazhongzhexue」
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突然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一词语,最早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使用此词的人为桑巴特。[1]]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当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逻辑构式中的釜底抽薪。其实,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是否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伪命题。在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原文文本中,我们会遭遇过去中文语境中没有出现的复杂词语构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civile(法文,市民社会)、kapitalismus(资本主义)-capitalisme(法文,资本主义)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文本中,上述词语从没有固定不变的简单语义;有的是,马克思在这一具体思想构境中不断变异的操作性话语实践。
一
“市民社会Ⅰ”主要指资本主义正式“发生”前,以政治为纽带的公民社会。这一政治学语境的概念在不同现实情境中发展出了两种理论趋向:一是建立在古希腊政治城邦上的公民社会,二是启蒙时代以政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Poltike Kornonia),是一个以正义为基础、呈现小邦寡民特征的,人们在以伦理为原则的法律体系中形成的城邦共同体。这一讨论视域经由拉丁文、英文转译为市民社会/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我将其划分为“市民社会Ⅰ(A)”。资产阶级启蒙后,公民社会开始向市民社会裂变: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的分工与商业开始兴起,新生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市民社会的现实主体从城邦的自由人转变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但这种市民社会的最早出现并非对应经济关系,而是指反封建反旧等级制的社会政治交往体系。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讨论域也从专制政治体转变到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体制的公共领域,少量学者称其为“布尔乔亚社会”(Bourgeois society),我将其划分为“市民社会Ⅰ(B)”。
之后,资产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团体,而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显现。于是,“市民社会Ⅱ”在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和古典经济学视域中得以呈现,使得洛克和霍布斯所说的市民社会概念背后的经济关系浮出了水面。古典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从重农主义发展到古典经济学,第一次透视了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古典经济学中,“市民社会Ⅱ”的概念首先在斯密《国富论》中完成了对市民社会概念从政治领域下沉到经济领域的转变。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从这种分工出发,实际导向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从个人来看,劳动分工实际上导致了劳动者本身只能满足他人的欲望,如果需求不能满足,就必须用生产剩余劳动去交换其他人的东西,于是劳动本身在这一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被碎片化了,需要的满足也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从社会来看,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斯密的语境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在前资本社会里面就是一个宗法制的共同体,而在斯密的时代却出现了以需要为基础的市场交换,也就是一个由经济必然性盲目起作用的被中介的社会。我认为,“市民社会Ⅱ”的原初发生语境就是由交往经济关系构成的原子化个人自发形成的社会。
也是在斯密的“civil society”转译为“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后,黑格尔以“市民社会Ⅱ”为现实根基,完成了从抽象到现实再回到抽象的辩证法体系,批判地发展出了“市民社会Ⅲ”的概念。黑格尔在双重意谓上批判继承了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的阐述:一方面,黑格尔敏锐地观察到了斯密的一个表述,即被斯密称为通过交换构建一个市场的依赖体系,这被黑格尔称为需要体系,也就是商业社会。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私人利益领域当中的需要以及需要的被满足。另一方面,如果给“市民社会Ⅱ”作一个分界,那么在斯密那里市民社会是肯定性的,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否定性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第二自然的典型表现,只有国家和法才是市民社会的前提与扬弃结果。因此,黑格尔走上了对市民社会进行唯心主义超越的道路,走向了自由王国,这也是马克思对其理性主义国家观进行颠倒的原因。
然而,在马克思早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市民社会Ⅱ”是不在场的,他更倾向“市民社会Ⅰ”的内容,因此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市民社会Ⅲ”的批判是一种伪颠倒。[2]首先,马克思在现实遭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倒逼他反思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试图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体系进行真正合乎人性的颠倒,这无疑是进步性的。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此时没有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内容,可能连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都没来得及认真研究,因此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303节的评论中说:“关于此,我们在之后的‘市民社会’一章中再继续研究。”其次,《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指的是法权意义上的市民团体,以及市民团体中的个人权利与个人幸福。刚从法学研究转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还不能透视到市民社会深层的经济学内涵,而只能辗转在直观的扁平化群体中,以此为基础来对黑格尔结构化体系进行颠倒的尝试无疑会面临理论之困。直到《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才关注到作为需求体系的“市民社会Ⅱ”及其批判性的“市民社会Ⅲ”,提出在政治立场上的资产阶级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最后,马克思不仅对市民社会作为现代国家的前提和动力表示了肯定,与黑格尔逻辑如出一辙的是,马克思对彼岸世界的悬设也寄托于市民社会对国家的超越及其自身的超越,最终只能落入思辨式人本主义的窠臼。但当我们从马克思的一生回过来看马克思的这一尝试,又必须承认,虽然此时的马克思没有进入“市民社会Ⅱ”的语境,但他以对物质利益的鄙弃为出发点来对市民社会超越的想法却贯穿其一生;在其深入剖析经济与历史现实的过程中,这一超越的想法将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二
自从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了经济学后,他才真正进入了“市民社会Ⅱ”和“市民社会Ⅲ”的发生语境。因此也是在1844年,马克思在人本主义视域中研究经济学,理解和丰富了斯密与黑格尔笔下的市民社会。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用德语摘录、法语插录了斯密《国富论》,以及法文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第一次意识到,现实的社会是斯密提出的在分工基础上进行剩余产品交换的现实商业社会,马克思将这种需求体系认定为德语的“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马克思在《巴黎笔记》摘录中所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工业生产为基础,马克思认识到,在当代社会,工业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却在评论中认为这是人的本质展开和实现的结果;二是在以交换和分工为基础的商业社会中才会形成人与人需求体系的社会,而与此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产生共鸣的是斯密的商业社会。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现实的人的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利己主义的私欲而交换劳动产品,不仅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且人与人交往关系被交换中介化了。这一观点也在马克思撰写完成《巴黎笔记》之后,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形成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摘抄的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但是马克思却在德语的评论中两次使用这个概念,特别是摘录布阿吉尔贝尔的时候,马克思评论道:“所有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一切的放任。在布阿吉尔贝尔那里和在其他人那里一样,物的自然进程(der natürliche Lauf der Dinge),即市民社会,将会赋予事物(Sache)以秩序。”[3]可以明显看出,尽管马克思此时对经济学的实际运行与实质内容还一知半解,但是他已经开始从这一客体角度去体悟市民社会的整体运行,即“看不见的手”所操控的人与人的关系。
与《巴黎笔记》的摘录不同,《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市民社会批判思路,以及马克思的另一个理论他者———黑格尔与“市民社会Ⅲ”———也随之浮出了水面。青年马克思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其实就是对市民社会现实的人本主义批判。让我们先来剖析异化劳动理论的构境。其一,与费尔巴哈和赫斯一致的是,马克思在心中设置了一个“应然”的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合乎人性的关系,所以市民社会应当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其二,马克思在现实的观察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现实并不是他设想的那样:在市民社会中,劳动者对象化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对象化劳动活动本身不仅不属于劳动者,而且劳动者劳动得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象化的对立,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其三,只有从异化扬弃和复归到真正的人的类本质,才能使人真正实现自我以及社会的共产主义。如果仔细甄别,不难发现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来批判市民社会的思路承袭自黑格尔,而非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不仅在批判对象上与黑格尔一致,即用批判性的“市民社会Ⅲ”来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市民社会Ⅱ”,而且在逻辑思路上也是一个从异化到扬弃的过程,只有价值悬设的内容与费尔巴哈更密切。但令人费解的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却鲜用“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为什么?我认为,马克思此时虽已开始认识到客体向度的“市民社会Ⅱ”,但古典经济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具有资产阶级的模糊性,所以直到手稿的增补中他才承认:“社会———就像国民经济学家展现的那样———就是市民社会,在其中每个个体是各种需要(Bedürfnissen)连结成的一个整体。”[5]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马克思在“市民社会Ⅱ”和“市民社会Ⅲ”的基础上,衍变出了“市民社会Ⅳ”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被整体表述,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被深化。在《形态》中,除了在政治立场的含义上使用“资产阶级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马克思更多是使用“市民社会Ⅳ”来进行完整的一般历史性描述。马克思首先对以斯密的“市民社会Ⅱ”为基础的“市民社会Ⅳ”有了一个肯定性的描述,前文曾经提到斯密“市民社会Ⅱ”的两个部分:一是在物质生产过程当中,劳动分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的碎片化,然后导致需要的不可满足;二是在交换领域交换的盲目性市场过程。斯密的论证是完整的,但是很多学者在研究斯密的“市民社会Ⅱ”的时候,只关注了他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交换领域的商业社会运行。而马克思在《形态》中继承了斯密的论述,其中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从流通领域走向物质生产领域。一方面,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市民社会Ⅳ”在当时的社会中“首先是伴随着资产阶级(Bourgeoisie)发展起来的,是直接来自于生产和交换而发展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构建了所有时代里国家和通常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Basis)”。[6]马克思对这种作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作了细致分析,他认为,特定的市民社会就是一定的交往关系的整体,其决定了整个作为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其实这一判断应该对应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基础,即现代经济社会形态的基础、经济关系的总体决定了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法意识形态,这一正确的历史性表述。但马克思却将这一判断延伸到了人类所有历史发展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形态》写作时期并没有研究所有历史的(包括原始社会)发展形态,因而他不可能发现原始社会中不存在“市民社会Ⅳ”这一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所以这里关于“市民社会Ⅳ”的历史性描述是完整的,却非完全正确的。随后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法语语境中深化了对“市民社会Ⅳ”的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使用“sociétécivile”(法语“市民社会”一词)来表述决定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使用“sociétébourgeoise”(德语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对应的法语词)特指封建社会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从此开始,马克思逐渐走向了聚焦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分析。
三
1847—1849年,马克思从经济和历史方面阐释了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sociétécivile的概念,即“资产阶级社会”。他聚焦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在经济学语境中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变革。《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面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问题的公开文献。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经历了漫长的酝酿、积累、诞生的过程,从刚开始的商业行为出现,到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到对整个封建社会进行积极性变革,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酝酿阶段;只有到了生产方式变革时,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才正式诞生。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神圣性、垂直性,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烙上了以金钱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特性。而《雇佣劳动与资本》及其手稿《工资》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语境探究资本关系的重大发现。“黑人就是黑人,在一定的关系中他首次成为奴隶。纺织机就是纺织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它才成为资本。”[7]马克思以黑人为喻,精确描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统治性力量———作为关系的资本。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的概念,但他已指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即看不见的资本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这无疑是颠覆性的。但马克思在这一崭新理论阐释之初也遇到了问题:资本关系是如何产生并成为统治性力量的?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只看到了表面竞争领域的资本关系结构,却无法解答生产领域的问题,因为这涉及马克思后来才创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所以,当时马克思再次回到书斋,写作卷帙浩繁的《伦敦笔记》,重新研究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理论,逐步发现资本关系的秘密其实在生产领域之中。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细致分析了资本作为社会基础的历史性发生,从劳动分工到社会分工的精细划分,慢慢走向现实“资本主义”的发生,最后产生了交换的必然性,即商品生产。马克思剖析了在充分的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的必然性,这比斯密、李嘉图在“市民社会Ⅱ”层面的分析更进一步,并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最后他激动地说:“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颜色,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8]为什么马克思会将资本比作普照的光?马克思曾经作过很多比喻,但是将资本比作普照的光是与之前完全异质性的比喻,它不是简单代表我们熟知的所谓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过去的死劳动。过去研究恰恰忽略的是,马克思既然要发现这个社会的本质,他就一定要关注有产和无产的财产问题,以解开“市民社会Ⅱ”的秘密。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社会,一部分人有钱,一部分人没钱;但资产阶级最精明的地方是使社会不仅在政治上看起来是平等的,而且在“市民社会Ⅱ”中,人们之间基于经济关系的交易也看起来是公平的,是一种你愿意卖我愿意买的公平交易。过去人们认为买回来的东西是劳动,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买的其实是劳动力的使用权,换言之,表面上看起来公平的经济交往和流通的背后实际上是生产领域。所以,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深入,到后来揭示了无偿占有生产过程当中的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不仅是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是马克思第一次对这个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所以,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
总之,“市民社会”的多重话语实践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开展,代表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思考对象和批判水平,而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喻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马克思才真正形成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参考文献:
[1]1976年4月,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作了三次学术报告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他当时已经基本完稿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1977年,该讲稿的英文版《对于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反思》(After 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and Capitalism)出版,此后又以《资本主义的动力》(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为名出版意大利文版(1977)、法文版(1985)和中文版(1997)。在这部讲稿中,布罗代尔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问题:“‘资本主义’一词,从20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02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Karl Marx)从未用过这个字眼。”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
[2] 详见张一兵、张福公、刘冰菁、孔伟宇:《“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历史语境”笔谈》,《学术界》2020年第9期。
[3]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Ⅳ,Bd.3/1,Berlin:Akademie Verlag,1998,S.53.中译文参见李乾坤、刘冰菁译稿。
[4]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Ⅰ,Bd.2/1,Berlin:Dietz Verlag,1982,S.391.中译文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
[5]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Ⅰ,Bd.2/1,S.429.中译文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0页。
[6]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d.3,Berlin:Dietz Verlag,1978,S.36.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7]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Bd.6,Berlin:Dietz Verlag,1961,S.407.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8]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Ⅱ,Bd1,Berlin:Akademie Verlag,2006,S.41.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来源:张一兵:《“马克思: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笔谈》,《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异宾(笔名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权威发布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资讯;
为读者提供第一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研究文本;
分享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投稿邮箱:xindazhongzhexue@sina.com
关注我们,过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