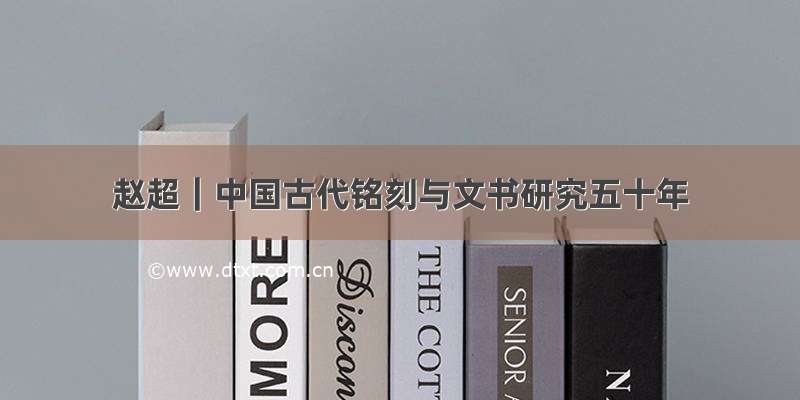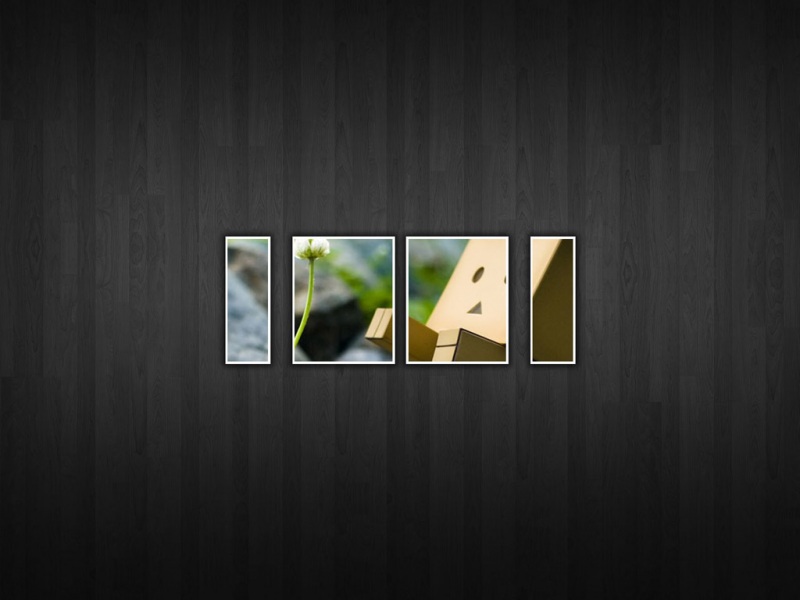「来源: |求诸堂 ID:inveni_zaq」
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书中的行在缎子
文/[日]森安孝夫著,冯家兴、白玉冬译
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
摘要: 伯希和编号敦煌莫高窟第181窟出土第193号和194号回鹘文书是记录物品发放的账本残片,年代属于元代。其中的qngsai是行在的音写,即南宋都城临安,今日的杭州。qngsai tavar即“行在缎子”之义,表明杭州产的缎子在元代已经流通于西北地区的敦煌等地。其背景是当时回鹘人联系网在中国内地的存在。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回鹘文书;行在;qngsai tavar
一、另一敦煌文书
1908年,伯希和(P. Pelliot)调查(之后获得)的敦煌文书概要报告从敦煌寄到了巴黎。此报告另有续篇称,在有别于所谓藏经洞(伯希和编号第163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17窟)的蒙元时代的两个窟(位于千佛洞的北部,内部装饰为纯西藏怛陀罗佛教样式)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属于13—14世纪的汉文、蒙古文(不是回鹘文!)、藏文、婆罗米文、西夏文的文书(抄本和刊本)残片。伯希和所获敦煌出土品,现在分别收藏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和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我于1978—1980年留学巴黎期间,有幸广泛调查伯希和带回的这些出土品,结果发现,在国家图书馆中除了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及其他文书外,还有伯希和编号第181窟及第182窟出土的汉文、回鹘文、蒙古文、西夏文的文书残片。另外,在吉美博物馆,除伯希和第181窟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约900个,在目录中误认作蒙古文!)外,还有在敦煌发现,但无法确定具体出自何处的回鹘文和婆罗米文的文书。森安1985年论文《ウイグル語文献(=回鹘语文献)》(以下简称前稿)以总览敦煌出土的全部回鹘文献为中心课题,同时根据以上事实和其他信息,主张:(1)伯希和在报告续篇中提到的“蒙元时代的两个窟”确实是指这个第181窟和第182窟;(2)王圆箓在首次发现藏经洞后到斯坦因及伯希和访问敦煌的7—8年间,将在第181窟和第182窟以及其他地方发现的贵重物品搬运进藏经洞的可能性很大;(3)指出出土于藏经洞的所有敦煌文献(及画卷)迄今一直被认为属于11世纪上半叶以前,但实际上其中混杂有蒙元时代东西的可能性极大,从而向敦煌学界敲响了警钟。只是上述(1)的主张必须建立在1908年伯希和尚无法立即区分以回鹘文字书写的回鹘语和蒙古语的前提下。虽然有些犹豫,但之后参与刊行Mission Paul Pelliot系列第11卷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的贝萨尔(R. Jera-Bezard)先生给我寄来了收录在未出版的第6册中的、伯希和关于第181窟的亲笔笔记的复制品。据此,得以证明我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其中不仅有与前面所讲的从“蒙元时代的两个窟”中发现物品的报告续篇的法语原文几乎相同的句子,而且还把那个木活字误认为蒙古文。由于在1908年的敦煌文书调查报告中,他还犯了将藏经洞本身存在的粟特文误认为回鹘文的错误,所以1908年时的伯希和尚没有当场识别用同系统文字书写的粟特文、回鹘文和蒙古文的能力,看来有将回鹘文误认为蒙古文、将粟特文误认为回鹘文的倾向。当时他年方29岁,尽管是个天才,但是在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词典的情况下当场匆忙写下来的。因此,在当时的笔记和书信形式的报告中出现这样的错误,亦不足为奇。
第181窟和第182窟出土文书的复原和再发现,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后代文书的“混入”。这不仅是迄今为止已经引起注意的回鹘文,还涉及到汉文、藏文、婆罗米文和绘画类等与敦煌学整体相关的重大问题。但是,还不止于此。我们通过对第181窟和第182窟本身及其出土文书的总体把握,开始向着迄今未曾想象到的“另一个敦煌学”(蒙元时代)的构建迈出了一步。在这一点上,我想通过上面言及的前稿及其补遗,以及通过活用拙稿积极推进研究的百济康义的诸论文,正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此我再次提出一个新的具体例子。
二、伯希和编号181窟出土回鹘文书No. 193 + No. 194
此处使用的文书是伯希和第181窟出土回鹘文No. 193组(No. 193 + No. 194) 。No. 193和No. 194肯定是从同一文书中分离出来的,但由于过于零碎,相互间的位置关系不明。即使看原文本,也无法判断哪个是正面,哪个是背面,所以将其中一个称为A面,另一个称为B面。No. 193和No. 194的A面是同一个人的笔迹,B面也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但是A面和B面是不同的笔迹。受篇幅所限,下文仅引用A面。
No. 193 A
1. ………………………………………//// tayingdu toγma
大乘都[1] Toγma
2. ……………………………………///WR atlγ bir aymaγ
叫……的一个爱马[2]
3. …………………………………//// ’sn tmür atlγ bir
叫阿贤铁木尔的一个
4. ………………………………………/// aymaγ ili alp
爱马的使臣[3]获取
5. …………………………///WN-nng qor bolm tavar-nng
的蒙受损失的财产的
6. ………………………………… ili-k alt ta bz-k
给使者 6 外棉布[4]
7. ……………………………… ü qap bor birl ayaq
3皮袋葡萄酒和盃一起
8. ……………………………… tidim-k ü qngsai tavar
给Tidim 3 qngsai tavar
9. ……………………………… ta bz birip·S"Y"/// ……
给[5]外棉布,
10. …………………… qngsai tavar iki torqu …………
qngsai tavar 2 绢
11. ……………………Z tavar bir torqu ////// ……………
tavar 1 绢
12. ……………………//YWDY/// "sn tmür …………
阿贤铁木尔
No. 194 A
1. T//// P/////………………………………………………
2. iki ta bz birdim ·/……………………………………
我把 2 外棉布给了。
3. ta bs bir i bz bir/// …………………………………
外棉布,我给了(?)1 内[6]棉布
4. yana bir q//l qngsai tavar ………………………………
又,1 q//l qngsai tavar
5. birmi a tavar torqu ……………………………………
给了的茶[7] tavar 绢
6. ta bz taypu-nng ol ……………………………………
外棉布是太傅[8]的东西。
7. bir str at mündür////……………………………………
把 1 两[9]放马上(送?)
8. -ta toγma-qa iki ……………………………………………
给Toγma 2
9. mal tmür …………………………………………………
所有物铁木尔
词注:
[1] tayingdu:这个人名在No. 193 B第4行中也有出现,在未发表的大谷文书Ot.Ry. 4570, Ot.Ry. 5292中也有出现。另见茨默论文。茨默未特意指出,但这毫无疑问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回鹘人名“大乘都”。其作为大乘都这个名字的实例,可以从程钜夫《雪楼集》卷8所收录的《秦国先墓碑》主人公中举出,是忽必烈的孙子安西王阿难答的佛教教师,出身于北庭的人物。
[2] aymaγ:爱马aymaγ是指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作为上至自治领、民族集团、部落,下至部队、氏族、家庭等大小不一的社会组织和军事、行政单位而使用的突厥蒙古语。最早可以追溯到突厥的翁金碑文。
[3] ili:这个ili“使、使者、使臣”指代什么是重大问题,现不考察。
[4] ta bz: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多鲁坤·阚白尔、克由木·霍加两位赐教,这个“外(棉布)”与下面词注[6]的“内(棉布)”相对应,分别是“面料用(棉布)”和“里料用(棉布)”之义。兹从此说。然亦不能抛弃认为这是“劣质的”之义的山田信夫意见。特别是山田认为与tas bz(粗棉布)相对应的ink bz“细緤(优质棉布)”存在于No. 193 B第9行中,故更是如此。
[5] bir-“给予”只是采用了原义,有充分的余地可以理解为“支付”“偿还” 。
[6] i bz:参见词注[4]。
[7] a:茶,《华夷译语》有实证。但是,-也许应该解释为“……的样子”。
[8] taypu:汉语“太傅”的借用词。
[9] str:从粟特语st"yr借用的货币和重量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两”。
那么,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在A面3处可以见到的qngsai(也可以读作qngai / γngsai / γngai)这个单词。这个词在以往的任何回鹘语词典,甚至在突厥语方言词典中都没有收录。
(1)No. 193 A 第8行,ü qngsai tavar
(2)No. 193 A 第10行,…… qngsai tavar
(3)No. 194 A 第4行,bir q//l qngsai tavar
后续的tavar原意为“家畜、活着的财产”,由此一般可派生出“财产、所有物”以及“商品、贸易品”的意思。而且这些词义至今仍为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突厥语诸方言所承袭。在我们的文本中,No. 193 A第5行的tavar是“财产”乃至“商品”的意思,但是(1)(2)(3)的tavar如果按这些意思来理解,则极其含糊不清,不能很好地与文本贴合。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与bz(棉)、torqu(丝绸)、bor(葡萄酒)、ayaq(杯,盏,碗)等处于相同级别的具体的商品名称。故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突厥语诸方言中,作为与我们的回鹘语(当需要与新回鹘语区别时,称为古回鹘语或中世纪回鹘语)关系最为密切的东部方言的代表,新疆的新回鹘语对此单词所给予的silk-stuff, cloth ,“杂色,多彩的丝绸”,或者说是“缎子”等意思,这是比“商品、贸易品”更加具体的意思。尤其是“缎子”,其存在可以追溯到清代的《五体清文鉴》,甚至与元代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明代前期的《华夷译语(高昌馆译语及畏兀儿馆译语)》 。联想起我们的文本是古回鹘语中最新的蒙元时期的文本,那么对将其中的tavar解释为“缎子”,应当不会有异议吧。
如此,qngsai在(1)(3)中,分别夹在ü(3)或者bir(1)这两个数词与名词tavar(缎子)之间。qngsai从词形来看不是动词的变化形(形动词),因此应该是纯粹的形容词或名词。另一方面,(3)中 q//l 这个单词在数词和qngsai之间,如果这是名词的话,那么在一个短语(one phrase)中就有3个没有表示领属关系词缀的名词连续出现,这对回鹘语来说是极其不自然的。假设q//l为形容词,那么它将落在“缎子”上。因此,q//l 除了qzl(红色)之外,别无他意。即,(3)是“一个红色的qngsai缎子”。连同(2)(3)综合考虑的话,首先可以推测到qngsai是表示形状、花纹和产地等的形容词或名词。而且,从语感来看,qngsai与其说是固有的回鹘语,不如说是外来语,特别是汉语的音写。亚洲内陆的回鹘人原本是从中国了解到丝绸,对他们来说丝绸属于输入品,并不是自产物(通常认为代指“丝绸”的torqu也是外来语)。何况缎子是高级绸缎,它的特定用语是固有的回鹘语单词,这难以成立。事实上,该用语在迄今已获发表的回鹘语文献中并未被发现。
三、qngsai即行在、杭州
那么,如果将qngsai假定为汉语的音写,会浮现出怎样的原语呢?我探索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那个著名的地名“行在”,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其根据是,第一,音韵上的完全一致。关于马可波罗(Marco Polo)作为世界第一大城市介绍的Quinsai(也作Quinsay / Qinsay / Kinsai等等)是指杭州(南宋时期的临安),学术界没有异议,但关于其原语有三种说法。即京师说、杭州说、行在说。据1957年发表名为Quinsai专著的穆尔(A. C. Moule)之说,京师说自16世纪以来在欧洲普遍获得相信,至今仍未消亡,但在学术上基本被否定。杭州说曾经是穆尔自己在1917年倡导的,但除了岑仲勉之外,并没有得到太多赞同,在1957年的论文中,他也已经不再坚持了。与此相对,日本的藤田丰八在1913年,那珂通世在1915年,桑原隙藏在1915年、1923年几乎同时开始独立倡导行在说。之后行在说在日本已经成为定论。而且,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力的学说。
不言而喻,“行在”是被金朝逐出南迁的宋朝,在恢复旧都汴京开封的夙愿之下,对临时设立的都城杭州所赋予的称呼,虽然绝对不是专有名词,但由于长达150年的习惯,它对当地人和外国人来说均成为一个固有的地名。正因如此,在元世祖忽必烈灭亡南宋之际,虽然下达了“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的圣旨,命令恢复旧称,但世祖时访问当地的马可波罗言其是Quinsai。此后,鄂多立克(Odoric,意大利人,1320年代访问杭州)称其为Cansay / Camsay / Cansaia / Casay / Chansay /等 // Guinzai // Ahamsane,马里诺利(Marignolli,意大利人,1340年代访问杭州)称其为Campsay,伊本拔图塔(Ibn Baūah,摩洛哥人,1340年代访问杭州)称其为Kh(a)nsā。此外,出任伊朗伊尔汗国宰相的拉施特(Raīd al-Dīn,1310年左右完成《史集》Jāmi"al-Tavārīkh)和历史学家瓦撒夫(Wassaf al Hadrat,1328年左右完成《瓦撒夫史》Ta"rikh-i Wassaf)都称为Khingsai(但瓦撒夫书中也写作Kh(a)nzai)。活跃于14世纪上半叶,并著有国际贸易指南书《通商手册》的意大利商人裴哥罗梯(Pegolotti)记作Cassai / Chassai,出仕马穆鲁克王朝的叙利亚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阿布阿尔菲达(Abū al-Fidā,1273—1331年)记载为Kh(a)nsā / Khinza 。不过,如果列举这么多,谁都会注意到,“行在”除了Kinsai系统外,还有Kansai(Hansai>Ansai)系统的发音。以往即使在采用行在说的人之间,对于如何解释这两个系统的存在,也没有准确答案。我很单纯地认为,这是从黄河流域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音(中原音)和长江流域以南的南方音(散布着海外贸易港的地区方言,即长江下游流域的江南音和更南边的福建音和广东音)的区别,两者是同时并存的。现在,虽然还没有找到正确地用字母抄写当时南方音的实例,但是在反映当时江南音的日本唐音(唐宋音)中,“行”读成“an”,例如行在(あんざい)、行燈(あんどん)、行脚(あんぎゃ)。在现代吴语圈白话音中,此“行”字一般都带有-a系统的韵母(不过杭州本身例外是-In)。现代广东话也发音作hang 等,无法批判我的推定——在南方行在读作Kansai系统是无稽之谈。但相比之下,北方的发音为Kinsai系统,这有确凿证据。首先,代表当时北方音的《中原音韵》(1324年成书)中的“行”被复原为君xi (hing)。现代北京音是xing (shing)。此外,在元朝末期的1362年建于河西永昌(甘肃省武威市永昌镇)的“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用汉文和回鹘式蒙古文写成)中,汉文的“行中书省”在蒙古文中没有意译,而是原样音写为qing ungu ing 。这个qing和我们的qngsai的qng只是转写上的不同,实际上是用完全相同的回鹘文写成的。“行在”的“在”基本没有问题,故在此附上。在同一个碑文上,不管是元代北京音,还是元代中原音,与“在”同音的“宰”都被音写为sai (蒙古文面第53行saisang=宰相) 。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在”有北方音的Kinsai系统和南方音的Kansai系统两种称呼,并且我们文本中的qngsai作为北方音的转写是无可挑剔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居住在杭州的人自己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城市的。如前所述,在现代吴语圈中杭州音是个例外,而且在反映元代杭州读书音的《蒙古字韵》(1308年)中,“行”用巴思八文字标作i 。也就是说,当地音不是南方的Kansai系统,而是北方的Kinsai系统。乍看起来,这似乎与我的看法相矛盾。然而在杭州这个大城市的上层知识分子阶层中,大多是过去从北宋都城汴京(开封)迁来人的后裔,杭州便呈现出一种漂浮在南方音中的语言岛屿的气象。鄂多立克、瓦萨夫和阿布阿尔菲达之所以同时转录了Kansai和Kinsai两个系统的叫法,不仅因为前者是通过南方海路流传下来,后者是通过北方陆路流传下来,难道不是还因为在杭州当地并用了这两种叫法的原因吗?
再者,把(1)(2)(3)qngsai视为行在的第2个根据是它与tavar(缎子)密切相关。在回鹘语中,先行的名词A修饰后续的名词B时,一般是A加上所有格的后缀+ning / +ing,B加上第三人称的所有(限定)后缀+si / +i 等,或者两者都加上。然而,在我们的文本中,A(qngsai)和B(tavar)都是孤立的,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紧密到不需要刚才所说的后缀的程度。
这样,不仅从语言方面,而且从实质上把两者联系起来也是很容易的。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是在全国范围内生产丝织品,但在高级丝织品方面,早在唐代,江南、剑南(四川)的产地数就超过了河北、河南。在宋朝,论产量江南(含浙江)亦居首位。就丝织品整体而言,宋代江南的生产额就已经有压倒性优势了。即使到了明朝,以南京、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位也没有动摇。由此也可以基本洞察元代的情况。进言之,如果把目光投向个别具体缎子上的话,在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可以看到作为南海贸易品的“苏杭五色缎”,同时我们也知道明朝内陆贸易点宣府镇曾有过“苏杭罗缎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些不仅是苏州和杭州生产缎子的说明,而且根据斯波义信和藤井宏的说法,在宋代丝织品开始显著商品化、按不同类别向特定产地集中、成为特产后向全国市场乃至国外市场流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些非常零星的史料中了解到,在元明两代,“杭州缎子”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国外都是著名的特产。正因为如此,对于回鹘人来说,没有必要特意说qngsai-nng tavar或者qngsai tavar,而一定是仅以十分熟悉的表达方式qngsai tavar就可以通用。
四、回鹘联系网的倡议
根据以上情况,很明显qngsai tavar是“行在的缎子”。反过来,以这个结论再来考虑一下No. 193组的文书,甚至包括它在内的伯希和编号第181窟出土文书全体时,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首先是关于年代的发现。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行在,杭州)是在1277年。在此之前,元与南宋是敌对关系,因此,很难想象持有南宋都城之名的高级丝织品,如此容易流通到敌国元朝,而且是边疆地带的敦煌。即,可以认为本文书的上限是1277年。在前稿中,我们已经得出了以下结论:蒙元时期敦煌的回鹘佛教的主角是(旧)西州回鹘王国人本身,第181窟是为回鹘人服务的,而且第181窟出土文书整体属于蒙元时期进行显著佛教活动的回鹘佛教教团。所谓蒙元时期,更准确地说是指从蒙古军队消灭西夏的1227年到元朝灭亡的1368年(或1388年)。进言之,在前稿的补遗中,我重新提出了更多新的史料并且反复考证,更进一步主张第181窟出土文书全部是14世纪初至中叶的东西。上限为1277年虽然不能充分强调这一主张,但也不与之冲突。1277年只是理论上的上限,从文书的性质来看,实际上年代应该更晚一些。总之,即便只了解到文书大概的上限,也可以对理解本文书内容以及对文书中出现的人名、aymaγ与ili等特殊用语提供考察的线索,这里就不赘述了。
接下来引人注目的是敦煌与杭州的联系。大岛(铃木)立子已经以裴哥罗梯的《通商手册》为基础,推定14世纪上半叶从敦煌经过甘州到杭州的道路,特别地被商人所活用,但同时又言“看不到记录下来的东西”。然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发现了“记录的东西”。这样看来,正如前稿所述,在第181窟出土西夏语佛典中,有14世纪初在杭州印刷、奉献给“沙州文殊舍利塔寺”的残片的事实,再次具有了重大意义。
姑且把目光转向外部,从敦煌回鹘佛教徒的故乡吐鲁番地区,出土有14世纪上半叶在大都(北京)、杭州一带印刷的几种回鹘佛典,以及13世纪50、60年代印刷的大都的回鹘人一家(丞相蒙速速一族)以佛教装束列队的木版画。此外,还存在活跃于江南并发财致富的回鹘人亦黑迷失于1315年左右曾派人去河西,给甘州和西凉府佛教寺院发放布施的事实。另外,如所周知,旧西州回鹘王国出身的武将、政治家、文化人世世代代活跃在元朝宫廷和江南。包括这些在内,如把迄今为止已知的回鹘人的活动舞台标出的话,如图所示。
浮现在这里的网络,是追寻偶然残留于史料中的极其零散的回鹘人轨迹的结果。虽然这完全是个偶然的产物,但实质上难道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我不这么认为。梅村坦早已追踪离开故乡、获元朝重用的回鹘人的活动,阐明他们当中存在为确保“血统的同一性”而保持同族之间结婚的强烈意识。基于此,元朝时期回鹘人之所以在各方面都扮演着显著的角色,是因为上面所看到的这种形式的网络,下至家族、一族,上至整个回鹘人全体,都被牢固地绑定,人、物、信息都能通过网络顺利地进行。说到同族间的联系时,马上就会想起犹太商人和华侨。即使没有那么大的时间和空间的扩展,但元代的“回鹘联系网”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史料中单纯残留商人活动的情况罕见,回鹘商人的情况也不例外。如果不设想到这种“回鹘联系网”和利用它所获得的巨大收益,就很难理解元代回鹘人的显著的文化活动(学术、艺术、宗教等)。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河西。不言而喻,那里在蒙古兴起以前是西夏统治下的地方,无论对于构成西夏核心的唐古特人来说,还是对于自古以来的居民汉人来说,河西都是一块不可替代的宝地。但是对于元代的回鹘人来说,此地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这是因为,由于海都之乱引起的大混乱,旧西州回鹘王室不得不将大本营从东部天山地区转移到河西。因此,恐怕有上万的回鹘人移居到了那里,而且大多数是佛教徒,还包括很多商人。当时的河西,作为连接对元朝宫廷产生巨大影响的藏传佛教的本土西藏和内地交通路线,以及作为从世界最大商业中心江南通往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在经济上、宗教(佛教)上、文化上无疑都占有极高的地位。如果去掉这样的河西,那么上面所见到的回鹘族之间的联系网就不可能成立。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本文最后提到的“回鹘联系网”这一命题,对于元朝史和回鹘民族史的理解到底有多大帮助,今后尚有待于各个方面的验证。对于第1节所述的“另一个敦煌学”来说,这也是无法忽视的。
[原补记]1987年9月初,我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的帮助下,得以研究墙面上残留的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等题记铭文和墨迹。并有幸解读了前稿《ウイグル語文献》以及与本文内容相关的一则回鹘文题记。那则题记位于第61窟甬道上,第61窟是在五代开凿,因中央有文殊菩萨而始称文殊堂,后来元代在窟前建有皇庆寺。这个窟也因描绘有与10世纪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曹延禄等有因缘的汉人、回鹘人、于阗人女性供养人像以及在内壁上画有五台山图而闻名。那条甬道被称为元代重修,其所绘西夏人供养人像“扫洒尼姑播盃子愿月明像”的左侧有此处所言的题记(右侧题记为蒙古文)。关于莫高窟的汉文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1986)已经出版。关于汉文以外的其他文种题记,据说也有同样计划,故此处恪守不引文本全文。不过,该窟是对一般游客开放的窟,而且已经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五》(东京,1982)图160(解说为第235—236页)中发表了略不清晰的照片,故引用部分内容概无大碍。在所有4行中,第2行写着bu manuiri bodistv-qa yüküngli“自从敬拜此文殊菩萨以来”,第4行写着qoo-luγ mungsuz abi qay-a bitiyü tgintim“高昌(即火州)人Mungsuz abi qay-a谨书”。如果这个Mungsuz是注39的木版画中的蒙速速(=孟速思),那就是一个大发现。即便此种看法无法成立,但至少元代吐鲁番地区(旧西回鹘王国)的回鹘人与敦煌有很深的关系的论据又多了一个。此次调查是在获得三菱财团人文科学研究补助金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该财团以及孙修身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后记1]本稿中首次使用的“回鹘联系网”这一抽象概念,与在地图上视觉显示的交流关系的回鹘网络相映成对。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利用当地出土文献论证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回鹘佛教徒在吐鲁番盆地和河西地区的活跃情况,进而凸显欧亚东部的回鹘网络,嘱托以后的研究者验证我所提倡的“回鹘联系网”这一命题对蒙古时代史和回鹘民族史的理解是否有益。幸运的是,其有效性被松井太和中村健太郎所证实,高兴至极。
[后记2]关于元代大都的回鹘人丞相孟速思一族以佛教装束列队的木版画的年代,森安2015年论文依福赫伯(H. Franke)和北村高1987年研究,取14世纪初之意见。不过,北村高在1993年发表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图版刊刻于1260—1267年之间。党宝海在2000年重新研究,重点依据孟速思自署丞相官号的年代,考述该木版画创作于1258—1260年的燕京。兹予以修正。另,关于本文原补记中提到的Mungsuz题记,松井太与其旁边的其他题记一起进行了解读。虽然明确否定了Mungsuz是侍奉忽必烈的有名的蒙速速(=孟速思),但就回鹘联系网而言,他提供了补充强调其不仅限于蒙元时代,而且还可以追溯到西州回鹘时代的新材料。即,他不仅追加了回鹘佛教徒串联起东部天山地区和河西地区,并进行广泛移动、交流的证据,而且还指出在蒙元时代,其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tangut lg,即曾经的唐古特人统治的西夏的旧领土,也就是元代的西夏中兴路—宁夏府路。
[后记3]也许完全是个偶然,当得知中亚—中国的丝织品相关图录中也使用了与森安1988文首次提及的“回鹘联系网”这一概念时,笔者多少有些吃惊。这是J. C. Y. Watt 和 A. E. Wardwell (eds.),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的第2章 “Kesi:Silk Tapestry”的“The Uyghur Connection” (pp. 61-62)一节,内容讲述西州回鹘和宋、辽、金、元朝之间通过高级丝织品刻丝、尅丝、缂丝(缀织)存在联系,其媒介是回鹘人。真是一个颇具意思的话题。不过,在森安2015年专著第116页中,莫高窟第409窟的著名肖像依然被视作西夏王。正如我所断言,此乃回鹘王 。之后,由于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已经普及,故如果将其作为资料加以引用,并结合坂本和子关于前近代中亚丝织品的研究成果,必能进一步加深讨论。
[后记4]围绕kinsai即行在说,最近发表有具有史学史意义的介绍,兹作引介:堤一昭:《石濱文庫所蔵の桑原蔵書簡──マルコポーロの〈キンサイ=行在〉説をめぐって──》,《待兼山論叢(文化動態論篇)》第46期,2012年,第1—20页。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