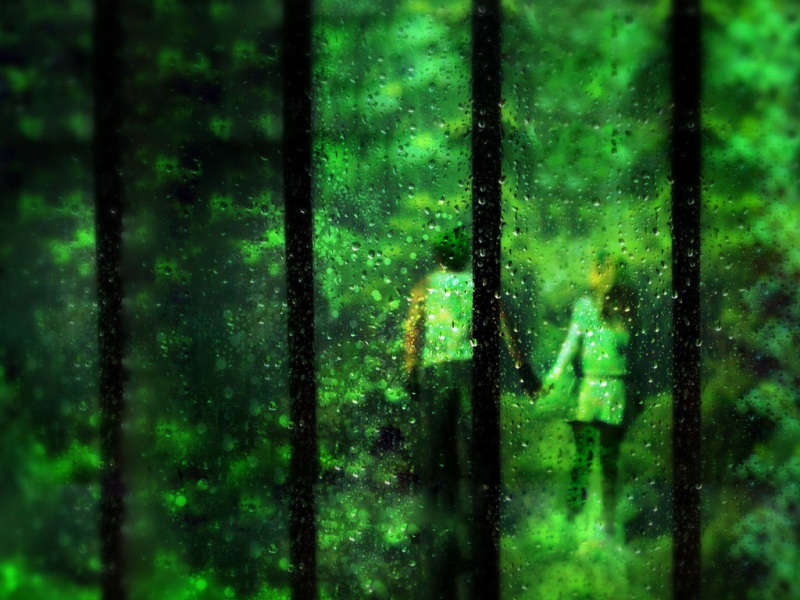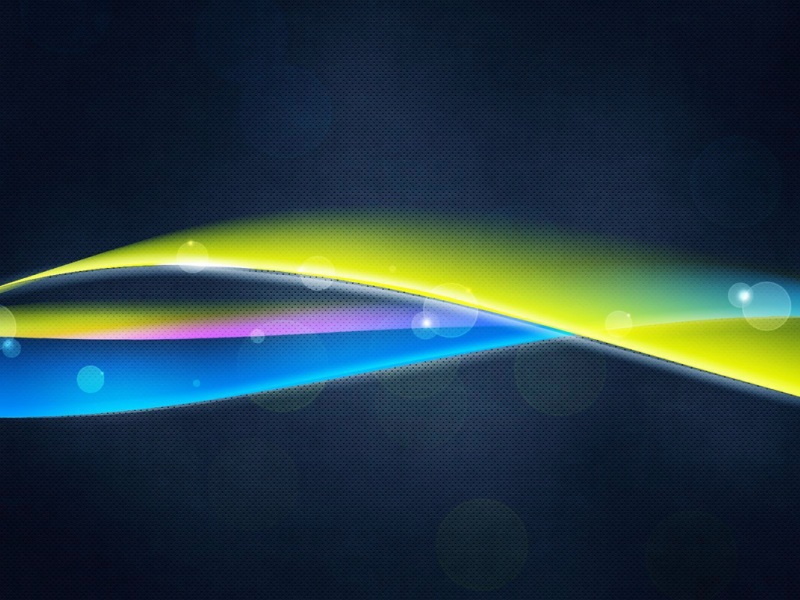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9584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0 分钟。
如何在强大的西方现代文化传统面前重新体认、拥抱中国自身的古典传统?如何跳出固有的抒情与叙事范式来重新安放当代中国复杂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体验?这些可以说是李修文近年的散文创作一直在直面、始终在思考的核心问题。继走遍祖国山河、写尽草木众生的《山河袈裟》(2017年)与饱览凡人苦楚、写透个人生活遭际的《致江东父老》(2019年)之后,李修文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延续性思索,交出了透着悲怆之气且带着赤诚之心的《诗来见我》。在书中,李修文或以诗为媒,书写自我与古今诗人相遇时互相“照见”的心迹与心境;又或者知人论世,通过将古诗“诞生”的情境与当下的人生际遇相连接,以“心象”风景的古今“参差对照”来为古典诗词注入时代新解。梳理作者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其书写的对象存在着一条从山河人间的“物”之“象”到思接千载的“心”之“象”的演变脉络。在此创作的延展线上来品读《诗来见我》,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何作家重新拥抱传统、寻找“古道与正统”力量的落脚点是“诗”?以诗为媒、以身作器的“诗来见我”式解诗,与中国古典诗论传统保持了一种怎样的张力关系?又彰显出李修文怎样的个体化诗学追求与美学品格?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主要探讨李修文如何以古诗词为中介来实现古今诗境的互文式书写,让中国古典诗歌由远渐近、由旧翻新、由客返主、由物及心,从而通向一种诗我互证的“心象”诗学的跨文体实践。
一、象其心:“诗”何以见“我”?
《诗来见我》出版面世不久,李修文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当被问及《诗来见我》的写作缘起与动机时,他回应指出:
“
因为这次疫情,我一次次强烈感受到了王船山先生所说古道与正统的力量:我们既要支撑住自己,也要成为支撑住这个世界正道的一份子。……中国古典诗词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密码。它几乎是我们的渊源、来历和出处,无时无刻不在证明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过去我们总是把诗词当做一门功课、学问去研究它,当然这也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人和古典诗词的相遇,应该是一种包含学问又不同于学问式的存在,它们是我们的生命证据。所以,我这本书实际写的是人与诗词的相遇,书名叫《诗来见我》。
”
“诗来见我”这一命名与命题,涵盖了诗人之象与作者之象的叠映与重合。诗歌的本象,是源自诗人的心灵之象;诗歌的再象,是李修文作为“读者”的心灵之象。所以诗来“见我”首先是指诗人之心、诗歌之情“照见”“点亮”了作者之“我”。而另一层面,“我”将自己投入到古代诗人们的诗境之中去重新发现自己、安放自己。王夫之有诗论云:
“
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博而不可得之象,霏微婉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栖,故诗者,象其心者也矣。
”
王夫之认为诗歌的作用在于表现诗人心中之“象”,是将诗人心中的想象、情绪、感觉赋形而外化于言。“象其心”说明诗是心与象的浑融统一。“心象”是一个尚未被经典化的概念,在古典文论体系中也很难找到它的位置。不过,倘若稍加分辨,可以把“心象”的概念离析出“心”与“象”两个维度。“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元范畴之一,由“象”还衍生出意象、兴象、气象等一系列子范畴。“心”“象”可以视作创作主体与客体,主体以象交流,以象达意,意由象显,象因意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主客关系往往被理解为心物关系,这可以理解为“心象”的传统诗学渊源。《礼记·乐记》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刘勰的“写气图貌,属采附声,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也”(《文心雕龙·物色》),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司空图的“长于思与境谐,乃诗家之所尚”(《与王驾评诗书》),近人梁启超的“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饮冰室合集》卷二《自由书·惟心》),这些论述都兼涉了“心”与“象”的维度。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借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及“造境”“写境”等概念来说明心物关系,他指出“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双会之际”,所谓的“境”,皆是心与物的统一。由以上论述可见,“心”与“象”的关系与“意”与“象”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象”由“心”生,“象”中见“心”,“象”为表现,“心”为主导。
文学创作“立象”而“尽意”的思维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心象思维”。这种创作主体内面的语词化,是一种融合了主体认知、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的心灵化的表象。在《诗来见我》中,李修文基于漂泊辗转的个人体验,来把握诗歌背后的诗人以及“我”遇见的各色人等的形象。诗人与他者在作者心中感性地呈现,这便是心象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心”参与“象”的塑造,“象”又投射到“心”中,“心”不是被动地呈现“象”,而是主动地选择“象”。心象包含作者对生活及人物命运的独特感受,它必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人物形象多被摄取为感性的、体验性的心象。所以,当心象转化为纸面上的形象后,但能够带给读者或是苍凉或是热烈的抒情氛围与阅读感受。作者以诗为媒,书写古今人物的心象,体现出“诗象其心”的诗学追求。
(一)以“诗”象“心”之发端
事实上,以“诗”象“心”的创作程式在 2017 年出版的《山河袈裟》中已初见端倪。《山河袈裟》中的散文主要分为叙事散文和知识随笔。在包含诗词的叙事散文中,诗词往往成为人物情感的变声。《长安陌上无穷树》中离情别绪在孩子的朗朗书声中弥散开来;《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痛失爱子的老路会随手涂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哀之语。作者并不是单单将古人的心性与遭际灌注到诗词中,使诗词沦为陈旧的俗言片语。而是在人物突逢变故、手足无措时,让映照着同样情境的诗词成为精神支撑的生命之舟。此种笔调,已为《诗来见我》的逶迤铺展埋下伏笔。在《阿哥们是孽障的人》的末尾,纷杂的场面袭向“我”的心头,“这错乱几乎使我疑心自己根本没活在这世上”“而是活在几千年里所有情义的要害里”。电光火石间,情深义重的事迹纷至沓来,在“我”脑海中明灭闪回。不过,“羊角哀找到了左伯桃栖身的树洞,范无救奔走在解救谢必安的河水中”,这种凝缩得只剩下主谓宾的故事,更像是呼之即来的符号。相比于《诗来见我》中《寄海内兄弟》一文对于元白、辛陈莫逆之交的动情描绘,此处“心”凌驾于“象”之上,“象”任凭“心”取舍。“他们是谁?”,“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作者展现了现实相遇之外的另一维度,即心灵相交,以今古联结的方式表达人物错综复杂的内心感受,正是作者朝向“心象”诗学实践迈开的重要一步。
在讲述他人故事的散文中,《未亡人》一文值得注意。此文依诗成象,用不同的诗句串联起苏曼殊的人生节点,笼统地勾画出了一个命运多舛的性情中人。作者的叙述语调是平静的,只是“实在喜欢”曼殊其人,远不及《诗来见我》中“我”与诗人惺惺相惜、血肉相连的深情厚谊。《山河袈裟》中带有诗歌元素的叙事散文,在发挥借助诗句文雅表达的作用之外,萌生了情动于中的“心”感与云雾迷蒙的人“象”。尽管二者处于分离状态,但已各具雏形,二者互相渗透、彼此联结,最终演化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心象”风景。
《肉体的遗迹》与《诗来见我》的末篇《最后一首诗》写的都是绝命诗,两相对照,可见“心象”诗学实践从发生到成熟的演变轨迹。《肉体的遗迹》的结束部分有言“她就来自我们中间,我看见的她,其实就是我自己”,这句话与《诗来见我》中的许多表述异曲同工,比如《犯驿记》中“多少人先在诗里看见了自己,继而也替自己找到了宽谅和解脱”,《枕杜记》中“在那些句子里,又有哪一字哪一词不曾见证我的八字以及山河众生的八字?”,诗句与个人体验的联结已悄然出现,不过作者随后笔锋一转,去讲无名氏的遗言,此处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到自身,并且一如既往的粗线条、快节奏地阐释着诗句。《最后一首诗》中,李清照、苏轼、永嘉诗丐都在苦厄缠身中保留人之为人的真气,也让“我”心意坚决;屈原、于谦、李白在认命与不认命之间挣扎,杜甫却能够吞咽苦楚、安定自身;病房大姐留下绝笔信,是在对抗遗忘,遗言得到回应,这足以安顿她一生的期盼与遗憾。心性各异的古人之象与悲欣交集的现实情景交相印证,作者以参差对照的笔法演绎了绝笔诗中异样的心灵图景。
《致江东父老》一书中收录的全是叙事性散文,作者致力于为不值得一提的人或事建立一座纪念碑。他以叙事的方式肯定旋生旋灭的芸芸众生,为一去不返的生命之流设立纪念。因此作者笔下的人物都面目生动、鲜活可感,嬉笑怒骂,无不令人动容。每一篇散文中,作者都陪伴人物走过一段路,同处在与命运抗辩的现场。这种心意相通从身边的人延伸至古人,发展至《诗来见我》以诗为媒的古今联结中,最终形成了以史鉴今为经、以“心象”共情为纬的诗学追求。
(二)诗与己,镜与像之周旋
《诗来见我》中有一篇《自与我周旋》,作者塑造了一个虚拟的他者,实现与自我的对话。作者在文中直言“诗之于我,是镜子,是鞭子,是手里的武器”,穿插着诗人们写给自己的诗,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解释了这三者的含义。贯穿这三者的内部逻辑是“看清自己、领受失败、寻求反抗”,即肯定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及对苦难的承受,寻求可能的超越。个人应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这是从古至今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诗来见我》全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书中没有给出本质意义上的答案,但是随着画卷的徐徐铺展,形态各异的“心象”呈现出来:有奋力抵抗、撒泼耍横者;有低至尘土、安定自身者;有真气尚存、白首忘机者。这些“心象”是镜子,映照出我们的处境,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扑灭妄念;它们是鞭子,使苦役现形,伤口处才能结成崭新的血肉和性命,振作起来,再度前行;它们也是手里的武器,阅尽千帆后才能超脱,再从荒唐里拂袖而去,找到亲手制造的生趣与生机。既要能吞咽苦楚,否则过刚易折,但又不能轻易妥协,否则生气全失。笔下的“心象”或有不同,但都试图指向同样的目的,即在风波之中修成不坏之身。
诗歌作为镜子,透过诗歌,可见百味人生、悠悠历史、浩荡山河。杜甫作为作者最崇敬的诗人,在书中出现频率最高。通过“我”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可知作者欣赏的诗歌之模样。“虽说人人都活在杜甫的诗里,但其人实在过苦,就好像,六道轮回全都被装进了他的草木一秋,最后,他也必将成为那个从眼泪里诞生的圣徒”;“那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所有人,这个人将成为所有人的分身而获得实在,所有人又将在他的布衣和肝胆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作者讲杜甫的诗歌,不提及他在声韵形式上的造诣,也不关注他精巧的诗歌技艺,作者在意的是“杜甫的诗歌包罗万象”。无名无姓的人们都可以在杜甫的诗句中指认自己,这才是慈悲之诗。换言之,作者选择的诗歌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曲尽人情之极致,任何人临镜自照都能够洞悉自己的处境。全书沿着从诗到人,由少至多的路径呈现了许多“心象”,在面临无边的广大时,外部的丰富与多元恰恰映照出自身的有限,从而疗愈自己的不甘。
鞭子或手里的武器都是破解生存困境的工具,它们自身必须是有力量的。作者以表现生命体验的最基本的词汇为每一篇散文命名,以这些词汇为中心来调度诗歌,因此诗歌中少有吟咏春花秋月的闲情雅致,多写锥心入骨的丧乱流离、相濡以沫的深情厚谊或是览遍河山的心如止水。文中选取的诗作不见得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千古名篇,但必然是诗人人生转折的注脚,诗句带来的不是凌空蹈虚的美感,而是粘连血肉的质感。在《唯别而已矣》中,作者写下:“这些年里,我所踏足之路,多是无名无姓之路,我所遭逢之人,也多是无名无姓之人,所以,在离别诸诗里,我总是不自禁地去着意那些无名氏们的句子。”籍籍无名的诗僧、诗丐与如雷贯耳的大诗人同时出现在文本中,如果说叙事是一种纪念,那么作者主动搜寻小人物的只言片语,分析为人忽视的假托之作,这便是对抗成见、争取发声的力挽狂澜。“我”作为各种情绪的感知器、各种经验的处理器,“我”的感受与体验是首要的选诗标准。诗歌的美学意义、哲思智慧、教化价值退而求其次甚至不作考虑。主体之“我”的凸显与高举,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来见我”。
二、悟其境:“我”如何“见”诗?
《诗来见我》对诗歌的解读与评论与古代诗论多有相通之处。语义繁难的诗词,作者解释大意;脍炙人口的诗句,作者另出新解;列出争论的观点,作者择优而定;介绍诗人的生平,作者“人伤其类”。“知人论世”是作者论诗的起点,诗人与诗句须臾不离、互相阐释。因此,作者既通过诗词与部分史料书写诗人心象,又通过心象赋予其他诗词新解。王夫之“诗象其心”诗论的要义在于“心”乃是万象之源。而“心象”之获得,则须加之以“悟”。由“感”而“悟”乃是“诗象其心”得以实现的途径。杨义先生在《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与基本形态》中指出:“中国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它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征,是以生命为内核,以文化为肌理,由感悟加以元气贯穿,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事实上,李修文《诗来见我》中对诗人“心象”的描绘,既是创作方式,又是解诗之学,其对中国传统诗学体系的继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平行性:诗境心境的同质“通感”
中国古代诗论的特征之一是平行性,其特点在于较少采用逻辑、概念、分析、推理等方式直接切入性地表达观点,而常采用一种平行的方式即如比喻、象征、类比、拟人、意境营造、暗示等方式来间接言说,并使言说内容与评论对象平行的特征。《诗来见我》以平行的方式论诗,作者不用专业的术语、概念去剖析诗歌、评判诗歌的价值、确定诗歌的意义,而是宕开一笔,娓娓道来与诗人相似的人物际遇,通过记录活生生的人的语言与行动,间接言说诗歌的真髓本意。
以《偷路回故乡》为例,作者列举了朱厚熜、裴说、尹廷高、韦承庆、杜甫、戴叔伦、崔涂这些诗人的诗句,提及了他们写诗之时的处境。文章最后一部分写的是“我”的几回在外过年的经历与感受,“我”与古人的处境相似,心绪相类,尽管古今场域在切换,但追寻妄念与摆脱妄念的张力始终存在。文本的后半部分,作者写道,“置身于如此境地里,我分明感到,我的周边里站着三个来自宋朝的人”,调转视角,是否可以说作者也站在那些思乡的诗人身旁呢?这是庄周梦蝶式的、“我”与古人的身心合一。平行放置古今人物的人生经历、在重合的生活片段中替换同质的心灵体验,这种平行对照为“我”打开了替古人言说的通道。
只要是评诗,就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诗算是好诗?作者虽没有直接回应,但他言明了不欣赏的对象,列举部分诗词来反向论证。《犯驿记》中,宋之问心术不正,用诗歌投石问路,至死未悔;《追悔传略》中,钱谦益的伤心诗中独不见一个“我”字,哀叹不过是尽个本分;《最后一首诗》中,纳兰性德自己的声音被花团锦簇的语汇掩盖,凑近去看却无甚可观。作者很少给予诗歌负面评价,从这仅有的三处来看,作者心中的好诗应当要去伪存真、言之有物,即“知耻之诗”。王夫之在阮籍《咏怀》其十二的评语中说:“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诗中有真情,读者和作者才能实现情感沟通。唯有诗词与诗人的生存境遇紧密联结,“我—诗人—诗词”的情感传导链条才能成立,“我”的言说与诗词的情境才能异构同质,而非错位背离。
(二)模糊性:形象喻示与心境弥散
作者的笔触透过繁复的史料,重点写诗人的人生转折与复杂心态。他先写类似处境中自己与身边人的感受,再推己及人,体味诗人的感受。“我”的形象喻示着诗人的形象,诗歌意义的谜团也迎刃而解。《雪与归去来》中,吴梅村被迫奉诏北上与“我”为谋生计奔走流离具有相似性,吴梅村是贰臣,“我”也是从前那个自己的乱臣贼子,我们都自惭、慌乱乃至恐惧,所以“我”深知他的“难堪”。《救风尘》中,韦应物的诗歌与“我”的遭际多次重合,《滁州西涧》的妙处众说纷纭,“我”却认为它写的是独处,能够吞咽并消灭耻辱与不堪,展现了救下一整座风尘世界的标准答案。这种形象喻示的平行性解读能够带领读者跳出字面意义,为体察诗人的心意提供了独特角度。然而,心境具有弥散性,当人处于某种心境时,往往以同样的情绪状态看待一切事物。作者常在解诗的过程中插入诗人与自己、他人的经历,与“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这种思路虽然殊途同归,但由于刻意强化感受的共通性,而消减了个体的特殊性,导致部分诗歌的意义被放大成为人生导“诗”。
作者常在段落间插入整首诗,不解释诗意,却无碍于读者理解诗词。《遣悲怀》中,曾经携手同游的知己,如今阴阳相隔,白居易的思念、感慨、酸楚、悲凉都倾注在“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一句诗中。当作者铺展开诗句产生的情境,诗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意义,字斟句酌地解释诗意只显得冗余。这种意义产生机制是感受性的,而非学理化的。
《诗来见我》中,作者通过横向与纵向两种路径解诗:其一是通过关键词横向串联内容相近的诗句与相似的人物经历。其二是以一个诗人为主体纵向解读他的诗歌创作。《枕杜记》《救风尘》《乐府哀歌》《墓中回忆录》《陶渊明六则》这5篇是纵向解读,其余15篇是横向解读。横向解读的文本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许多意义相近的诗句串联起来,但它们的区别如何体现?《遣悲怀》中,“近似之境,鱼玄机遇见过,所以她说:‘珠归龙窟知谁见。镜在鸾台话向谁。’顾贞观遇见过,所以他说‘依约竹声新月下,旧江山、一片鹃啼里。’‘郊寒岛瘦’里的孟郊也遇见过,所以他说:‘山头明月夜增辉,增辉不照重泉下。’”千姿百态地表达相似的情感,这正是诗词的魅力所在,然而作者却将这些诗词提纯成了情感的结晶。俞平伯说:“解析者,创作之颠倒也,颠倒衣裳,倒颠裳衣,一化为多,将繁喻简也。然而不然,苟以多为一,以繁为简,则又断断乎不可,此所以修词文法等虽列专科,而与制作之本终隔一尘界。”批评家是一化为多,将繁喻简;画家诗人制作家是多化为一,将简喻繁。后者损之又损,前者益之又益。作者进行诗歌批评,却对诗句的意义损之又损,形成了内在的悖逆。这是因为作者既是批评家又是创作者,诗词既是解析的对象,又是再创作的材料。“我”的身份转换决定了诗词需要随文本而曲折,因此“我”的诗论具有模糊性。
(三)整体性:气足神完的生命感悟
平行性的思维特征也必然显现为平行性的话语特征,即间接的、迂回的、模糊的、诗性的表达方式。与其说这是古代文论基于语言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使用的话语策略,毋宁说是一份不忍破坏生命整体的诗意。尽管书中的诗论充满了朦胧的印象、模糊的描述和感性的言语,“那是一种散点透视式的世界感受,它与‘道生万物’所描绘的世界生成模式和‘月映万川’的呈现方式是一致的”,这些话语最终指向诗歌与世间万物的整体性。无论是横向解读还是纵向解读,都有鲜明的线索串联起诗句,字词句义、作者心态、前人评价、“我”的经验,这些是作者论诗的四种材料,他从未对诗歌进行过切入式的分析,保存了诗句气足神完的状态。
《诗来见我》的腰封上有三句推荐语:他把命放在诗里,他让那些诗句有了热血和魂魄;打动无数作家和读者的生命书写;我所写下的不仅是我的审美对象,更是我自身命运的一部分。句句不离一个“命”字,这正是“我”的诗论与其他诗论的根本差别。古代诗论有两种路径将诗与人联系起来,一是“文如其人,作者的性格和作品的体貌表里相符,同质平行”;二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古代诗论的整体性是外在的,诗论中诗、人、自然的平行置换最终导向的是意与境谐、天人合一。在“我”的诗论中,当今的人与古人是平行的,古诗词却内嵌于“我”的命运。
“
我写的这些诗人,当我去触摸他们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是来自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诗所展现的是我们在日常当中所受过的苦,以及在苦中如何支撑下来,并且获得了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握手言和。
”
作者“我”的诗论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它指向诗词与生命个体的相遇,在它们指认彼此的过程中,诗词照亮了“我”的奔波之路。
三、融其体:“修辞立其诚”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回答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诗来见我》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是写“我”辗转奔波,抒发万端感慨的散文?还是记录不同诗人跌宕人生带有虚构性的小说?又或是评析诗歌、臧否诗人的当代诗论?对此,李修文曾在访谈中表示文体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最终产生的美学上的真实能否逼近我们内心的真实。“我是要写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哪一种文体去写作。对于我来讲,唯一的真实就是无限真实的精神个体。”
李修文一再强调的“内心的真实”与“无限真实的精神”恰恰是其“心象”诗学实践的原点。它既是解诗方法,又是文本延展的路径。“诗来见我”之“我”,再精准些即是诗来见我“心”。“在‘物竞天择’的全球格局里,脑子要足够坚固方能保证思想的生产,应当像‘机器’一样,而传统的‘心’似乎因为过于肉感脆弱而被取代了。”《诗来见我》的诗学追求则体现了作者向传统中国“心”话语的回归,正所谓“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心者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所以当作者在抉择的关口犹豫徘徊,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思虑再三的利益考量,而是心境的豁然开朗。《诗来见我》中没有细腻的五感描写,五感最终都归于心感。
《诗来见我》表达的是作者自我开解的生命体验,其中融入了一个现代文人对古典传统的执着追求。因此,作者通过跨文体实践融合多种质素,给散文创作带来新的生命力,这是写作技巧的拓新,并非是作者兴之所至,消解文体。每篇散文中并置着三“境”——诗境、情境、心境。而林林总总的诗境、跨越时空而平行的情境,最终由“我”的心境统摄。换言之,“我”的解诗求内心之“真”甚于求读解之“善”。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在提出“诗象其心”诗论观点的同时,亦言明“唯其有诚”乃是一切“心象”得以成立的基点。他指出:
“
耳所不闻,有闻者焉;目所不见,有见者焉。闻之,如耳闻之矣;见之,如目见之矣;然后显其藏,修其辞,直而不惭,达而不疑。《易》曰:“修辞立其诚。”唯其有诚,是以立也。
”
一切“心象”皆出于“诚”。“‘诚’者,心之所信,理之所信,事之有实者也。”前述李修文在访谈中所坚持的“美学上的真实能否逼近我们内心的真实”这一创作原则,正对应作者对散文文体认知的更新,诗论与叙事这些新元素最终服务于表现心境的艺术效果。诗境与情境展开了作者自我说服、自我评析的必经之路,跳出文本,笔下文字即是心底风波,千种风景、万种人生尽是“心象”风景。
再回到开篇时提出的问题。当下中国的文化格局正处在两个传统的纠缠之中,一个是东方古典文化的传统,一个是近代化进程以来我们所接收的西方现代文化传统。一方面,我们无法回归一个完整的东方传统成为自己的异己;另一方面,我们又终究还是熟悉的西方文化的陌路人。面对二者的拉扯,对于如何重新辨认、确证自己,找到自己的文化根脉与生命价值,李修文在《诗来见我》中给出了他的回答与路径:那就是回到古典诗歌。他试图通过重返古典诗词“发生”的现场,来思考面对西方理论话语体系时如何重新确立现代汉语的诗意;通过与古典诗词的相互照见,使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诗人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并在对诗词的复写、重释与评点中来激活诗教传统的诗性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诗来见我》的写作目的不是记录好故事,更不是学理化地解读诗歌,而是带领读者踏上这条联通古今的心灵廊道,观照他人亦反思己身,在古典传统中寻找与自我和解的路径,从而在波诡云谲的现实生活中、在顺从与妄念的撕扯中安顿身与心。
(本文刊载于《写作》2021年第4期。本期目录链接:)
原标题:《裴亮、张琪:诗我互证的“心象”诗学实践——评李修文《诗来见我》》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裴亮 张琪:诗我互证的“心象”诗学实践——评李修文《诗来见我》》,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