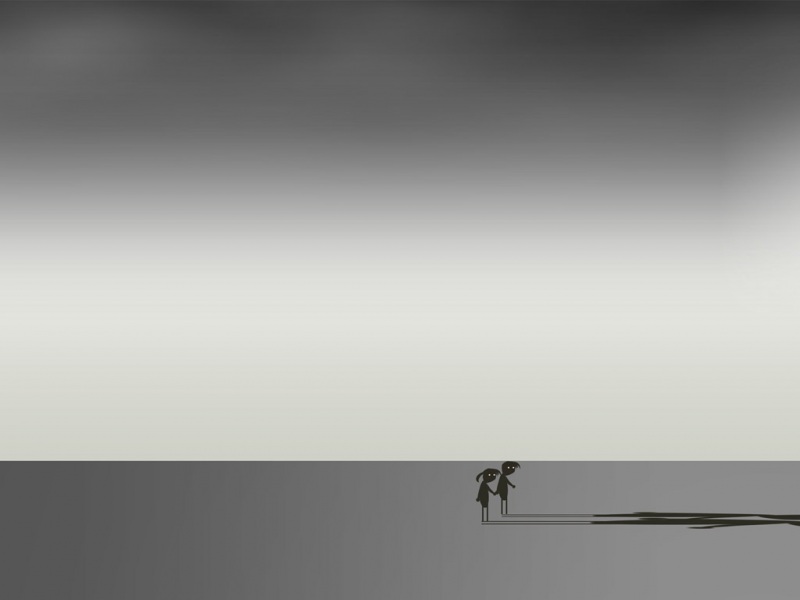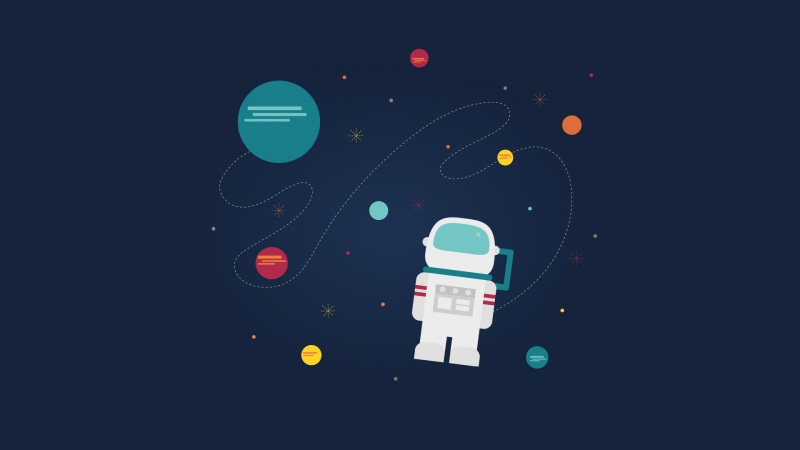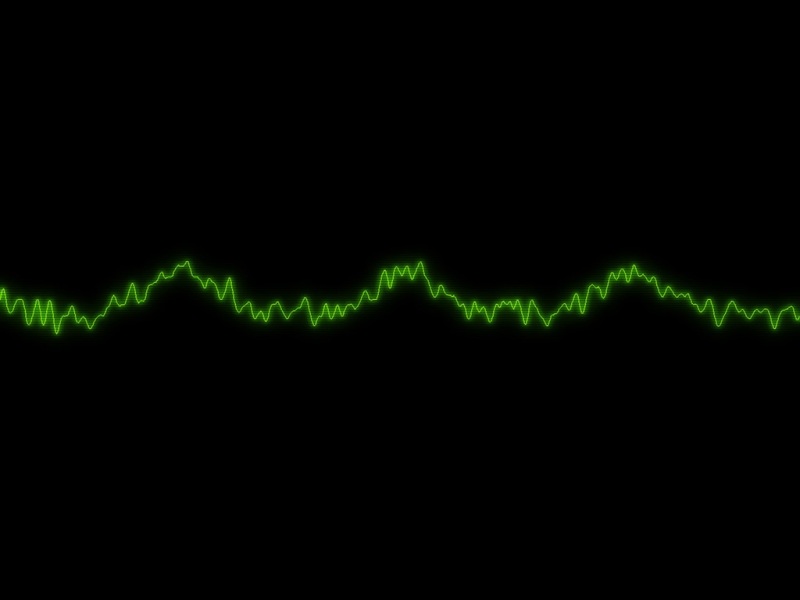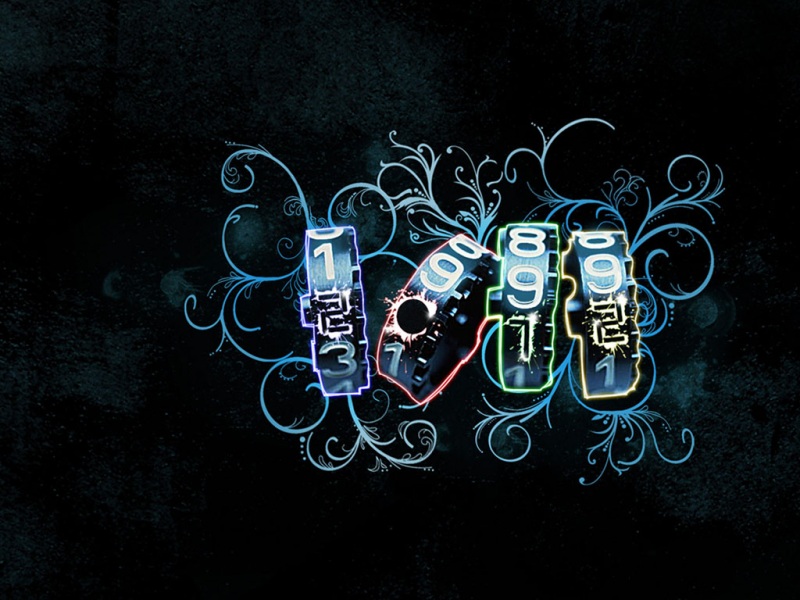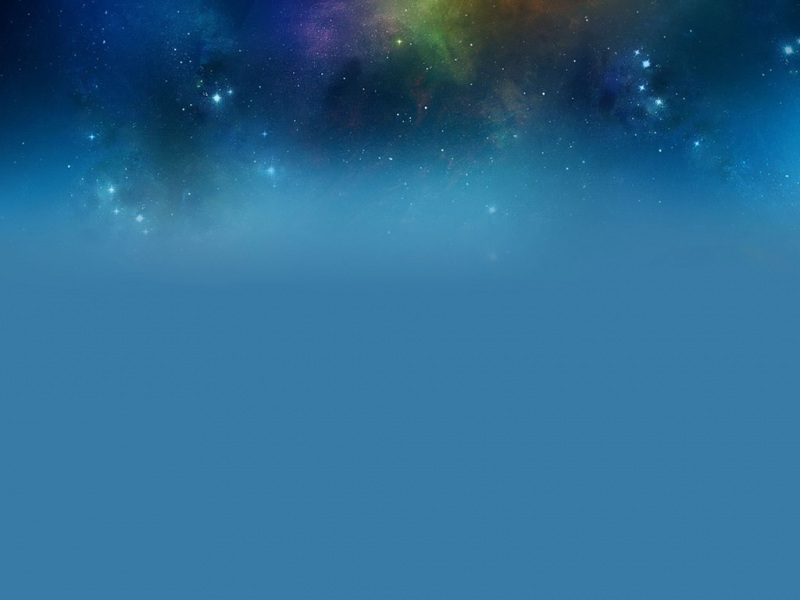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10135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1 分钟。
【编者按】
武汉大学文学院张箭飞教授的研究方向为“文学与风景”,目前正在翻译和校译译林出版社的“风景诗学”丛书。本文刊于邹赞、朱贺琴等著《涉渡者的探索——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名家访谈录》(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高晓鹏、李红霞对张箭飞教授的访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张箭飞(图片来自网络) 高晓鹏、李红霞(以下简称“高、李”):张老师,您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特殊时期,能与您展开这次云上访谈。自去年以来,您作为武汉大学对口支援新疆大学的天山学者,多次参加我们学院举办的论坛、主题会议、系列讲座等。这里,首先向您表示我们的真挚感谢,感谢您深度介入新大的学术生活和文学院这次安排的研究生学术创新活动。
我们都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风景与文学,而新疆这个地区有着丰富的风景资源,在您的研究方向之下,根据您的个人经历和学术积累,您能谈谈可以着手研究的方向,或者突破口在哪吗?
张箭飞(以下简称“张”):很荣幸接受这次访谈。自成为新疆大学编外一员以来,随着越来越了解你们的学术传统和优长,我越来越想将自己既有的研究与新疆风景资源对接。这里,我特别感谢新疆大学给我这个学术更新的机会,虽然机会总是意味着压力。我很庆幸自己能被新任务“倒逼”着跟进新材料,升级相关问题的思考。
武汉封城期间,我有幸参与你们学院的系列讲座。始料不及的是,讲到第四场,你们居住的城市也因为疫情发展受到较大影响。通过社交媒体,我发现新大同事要比封城早期的我们更加从容淡定,也许因为有武汉经验铺垫?你们笃信尘埃终会落定,也许因为傍依天高山远地阔的壮丽环境而心境安然——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与人类性格及心理的互相塑造关系,本身就是人文地理学或风景学长期关注的话题,而特别的事件,比如,突发的瘟疫或决绝的封城,会更加突出城市(风景)气质和居民行为的同构性。
前一次,在“风景作为观看的方式”一讲中,我重点讲到了鸟瞰和透视这两种主要观景方式——透视主要针对的是如画尺度的风景,如小桥流水人家、田畴村道旅人这样景深和景缘历历在目的风景,而面对天山、祁连山、秦岭这样连绵高耸目不可尽的山系群岭,也许鸟瞰是最佳的观看方式。
我查阅了一些材料,发现新大已经有人在做山系研究,比如,邹赞教授近年关于天山题材的影视作品研究,虽然主旨意在军垦历史、文化记忆、情感政治等,但已兼论风景的塑造力量。我注意到邹赞教授的中亚电影研究系列论文,那篇《历史记忆、文化再现与风景叙事——聚焦吉尔吉斯斯坦近十年重要电影》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一些观察和思考给后来者预留了跟进的线索,如“吉尔吉斯斯坦电影特别注重对‘如画美"和‘画境游’的影像建构。一方面,影片以‘本土’与‘地方’为视角,以当下世界现代性景观为参照,融自然风貌、民俗文化、民族审美于一体,图绘吉尔吉斯斯坦由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表达一种对‘如画’风景充满向往的‘恋地情结’。另一方面,电影持续发掘‘山地之国’自然文化资源的丰富意涵,启用外界对于中亚地域风貌的奇观心理与陌生现状,打造一批具有国家形象建构意义的风景符号”。[1]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弥补了很多内地读者认知空白,也预留了跟进研究的可能。说实话,我本人从没看过吉尔吉斯斯坦电影,尽管知道天山逶迤跨境西去,“把一半的美给了吉尔吉斯坦”,辉耀了半个盛唐的“天山明月”最佳赏月地点或许也在那边,而非这边的祁连山,这一现象促使我确信:文学研究只要涉及到风景、人文地理或环境议题,一定会与研究者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及在地(localization)资源发生关联,而一旦以新疆风景为起点展开跨学科的纵深研究,在一手资料、田野调查和风景感知方面,新大天然地具有优势。所以,自去年年底,我就开始琢磨能不能从天山风景着手,与新大同事进行切磋?在我看来,“新疆是个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这首著名的民歌起首就点明了“天山”的重要性:它是新疆成为一个好地方的风景要素。
高、李:提到山,中国名山真是太多了,关于山的名诗数不胜数,比如“一览纵山小”的泰山,“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等等,尽管有南北和高度差异,但往往给人一种“旖旎”和“险而不怖”的审美舒适感。然而,一旦写到天山,大多数与苦寒环境、战士戍边关联,比如,“天山雪云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让我们感到天山的寒冷与壮美。那么,您是从哪个角度理解天山的?
张:说到天山,我的第一印象来自媒体。网上有不少文章讨论能看见雪山的中国城市有哪些?拥有都市雪山的乌鲁木齐、成都、拉萨谁最“豪横”?就我个人而言,被众多雪峰环绕的乌鲁木齐肯定碾压成都,一个声称肉眼能见10座雪山的盆地城市,毕竟“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成都胜景有个苛刻的气象限定条件,只能在“晴好的日子里”看到贡嘎雪山、峨眉雪顶、四姑娘山雪峰等,这就意味着一年只有25个晴天的成都眼福大大低于天气以晴好为主的乌鲁木齐。即使与把整个玉龙雪山搂入城中的丽江相比,与坐落在高原雪域的拉萨相比,乌鲁木齐依然稳居榜首。天山横贯东西,高大绵长,构成最美的两面雪屏,人们推窗见山,抬头见山,天山无处不在,随时可赏——乌鲁木齐人最值得我们艳羡:几乎日日与壮丽的博格达雪峰相守相看,领受自然的美学滋养。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人人熟悉的大白话也可以转述为风景学领域的一个共识:“人是风景的作品”。因此,我也许可以推论:疫情期间新大同事所展现出的从容状态部分拜崇高的天山所赐。
天山 高、李:天山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审美对象,能够挖掘的内容也有很多,而且山作为我们中国传统诗学里的重要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辽阔的中国大地很多部分就是山地,群山和河流养育了我们伟大的文明。不同于欧洲,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开始了山之崇拜,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将仁与山联系起来,而那句日常用语“高山仰止”最能说明山在我们心目中的伦理价值。此外,不少地区的山葬习俗更是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观念。那么,在天山风景这个话题之下,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作深入的探讨?
张:如你们所说,天山是一个巨大的审美对象,影响了新疆人民的美感生长。新疆之内许多地方,比如库车、哈密、阿克苏都能看到天山的存在。这里,我想套用康德的一个名言造句:头顶上的天山,心中的新疆。换到其他区域,没有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敢说自己拥有一个全域“共看”的高山或山系。比如湖北境内的华中屋脊,仅被神农架地区的人看见,而其他地区的人对它只能可想而不可望。
说到如何研究天山,进入的角度实在太多,有些海外学者的史地研究成果堪称一种探索侧光,我们不妨借来一用,比如松田寿男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根据我的阅读心得,我认为可先从风景学的三个关键词进入,确言之,接近崇高的天山这一巨大对象:空间想象、地方感知和文学再现。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高、李:空间想象、地方感知和文学再现,您提到的这三个关键词,我们非常感兴趣,它们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概念的链条(chain of concept),合围包抄天山这一崇高客体(sublime object)?
张:是的。首先,空间这一概念,我曾在之前的演讲介绍过相关的解释,其中北美人文地理学界的宗师级学者段义孚先生的观点颇有启发意义。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段先生开篇就直接定义和甄别“空间”和“地方”这一对人文地理学的基础性概念(其实,它们也是风景研究或环境美学的基础性概念):“我们都生活在空间之中……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空间和地方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空间和地方》,第1页);在《风景与权力》里,主编米切尔教授则把空间、地方、风景当成三个可切换使用的词;而我对二者的转化(transformation)过程更有兴趣,也即空间如何转化为地方,地方如何转换为空间——只需要好好读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基本就能了然在胸。黄沙梁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一个“受到保护的,自给自足的小世界”,满足了他“对诸如食物、水、休息和生殖等的需要”(段义孚语),通过他的风景叙事和想象,这个实存于沙湾县四道河子镇的地方转化为一个遥远而浩瀚的空间,位于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万里之外。对很多读者而言,它可能就是一种无从抵达的万里之外,“引起空旷而无限的感觉”(段义孚语)。而这种感觉常常就是空间想象,对遥不可及的地方展开想象。就是发誓一辈子不想离开黄沙梁的刘亮程也曾想象过:“村庄上空飞过的一群苍蝇对应到世界另一地就是一群庞大的轰炸机。”刘亮程谓之的“世界另一地”其实就是他大脑创造出的抽象空间,“用心灵的眼睛设想的全景和无边界的空间”(段义孚语)。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当然,一度的万里之外也可转换为朝夕相对的地方。例如,一个外地人迁移到了曾是地图上一个抽象空洞的空间,逐渐与当地的文化产生了交融和认同,进而将生活的地方转换成自己的价值维系之地,变得像刘亮程一样,“紧贴着地生活”,感知地方的一切:壤土、水、空气、天空的每一朵云、炊烟中人说话的声音……他的体验和认知就是风景学所定义的地方感知,而敏锐的地方感知通常只有当地人才会具有。在大部分情况下,对一个不可企及的空间,比如天山,如此遥远,如此高不可攀,外地人只能展开想象,不会像游牧其间的哈萨克人那样自然而然地视某个牧场为自己的家乡,并产生强烈的恋地情结。以我为例,有幸为新大工作,每次匆匆而来,匆匆离去,对天山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很难转化成新疆作家笔下的那种地方感知——无论是刘亮程,还是李娟,作为当地人,他们沉浸于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越来越理解地方的意义。对他们而言,黄沙梁或阿勒泰就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地方”。与他们相比,我所拥有的只是空间想象或学术想象,我可以通过阅读天山的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献积累对它产生了解——也即在概念的层面认知天山,但不可能拥有邹赞教授的审美优势:推窗即见博格达雪峰,尚可利用短暂假期到东天山的江布拉克或伊犁河谷小住,或通过视觉、听觉等感知天山,积累丰富的风景经验。一点都不夸张地说,长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他甚至能听到天山的声音,它的风声,雪崩的声音……
说到听觉和声景,我觉得刘亮程写得最好。有批评家说哈代写出了威塞克斯(Wessex)这个地方每棵树发出的声音,其实刘亮程的耳朵也像哈代一样敏锐,他摹写的风声具有高度的辨识性和地方性。在空旷荒凉的沙漠边上的村庄,声景格外突出。我特别喜欢他那篇《我认识那根木头》,就是因为他高保真的“录音”水平和文学再现能力。
谈到文学再现,不免会讲到当下的文学研究趋向,它早已从经典文本或纯文学文本批评转向更有文类兼容度的文化批评了。面对天山这个文学的巨大对象,文学再现的范围更广,样类更丰富,确言之,再现天山的文类除了纯想象性作品,还包括散文、游记、田野调查、新闻报道等。我查阅了一些晚清民初时期赴任新疆的内地官员和考察西北的历史地理学家的游记、日记。出于某些原因,他们的西行漫记可能写得简略甚至枯燥。但是,即使寥寥几语,哪怕只谈到天气、路况、打尖歇脚,如果我们仔细爬梳,还是能找到很有价值的材料。关于天山的文学再现,我特别留意了三个江南作家:洪亮吉(1746-1809)、汪曾祺(1920-1997)和沈苇(1965- ),由江南美感陶冶出来的作家如何观看天山,他们的空间想象和地方感知值得深入研究。
有本辑入“西北史地丛书”的《新疆游记》引起我特别的注意,作者谢晓钟(1887-1948)是著名的边疆史学家,他在“横渡天山及哈萨克风俗”这一章描写了以崇高美为主的天山风景多重面相:优美、如画、怪异等,其中,五月二十二日日记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初春天山行旅图,“无穷无尽的空间得以伸展开去……使我们在每一个转折之处都获得一个全新的视野”(苏立文语):“发济尔噶郎,循河南岸,正东行。三十三里,过济尔噶郎桥,架木为之,旁无栏杆,宽不三丈,水流澎湃,声激若雷,滩石磋硪,状极可怖。岸皆悬崖,北面犹陡,偶有疏失,即足丧身。过桥折北行,微偏西,十里,升陡坡。此处有路通济尔噶郎,较过桥近十余里,近以冰消水涨,未敢冒险凫渡。五里,阿克布拉克,译言浊泉也。千户长沙脱巴勒提(领百户长十一,有牲二万余头),于此备宿站,以时太早,尖毕复行。初折东入山,山谷幽邃,比于函谷,渐行渐高。五里,乌鲁布拉克岭巅。下陡坡,更斜下极陡之坡,右临涧底,何止千仞,鸟道一线,宽不盈尺,设一堕崖,人马立碎。一里,危坡尽,地稍平,有泉汇成涝池,芦苇丛挺,青翠可观。循左山麓行,下长坂,右临深涧,其岸壁立数丈,如地新陷入者。两山哈萨所筑冬窝土屋,无虑数十。十二里地势渐阔,一望新苇,仿佛仲夏江南之稻畦。”[2]
谢晓钟《新疆游记》 高、李:在谈到天山风景的时候,您反复用到了“崇高”一词,关于崇高的讨论,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而且“在西方,‘崇高’概念与阿尔卑斯山相关,它使这个概念在欧洲语言中开始转向‘自然’。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座神山,可成为灵感之源”。[3]今天我们正探讨的天山,可以说是新疆的象征。崇高属于美学范畴,那您是如何看待天山与崇高的关系呢?
张:天山大气磅礴,风景整体无疑具有崇高美特质。不过,它的很多局部又具有优美、如画、甚至怪异(grotesque)的特点。可以说,天山能将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四大审美范畴可视化为最有说明性(illustrative)的风景范例并且丰富它们原有的定义。当然,天山给予观看者的支配性美感是sublimity(崇高性)。某种程度上,天山等于the sublime (崇高美)。看懂了天山,也就理解了崇高美的定义、内涵及外延。在我看来,近距离观察或者(有幸)走进天山胜读很多美学专著。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提到哈罗德·布鲁姆,他在《西方正典》里反复强调的一种阅读方式对我影响甚深。他说你不要用弗洛伊德(也即精神分析学)解释莎士比亚,而要用莎士比亚解读弗洛伊德——这一卓识形成于大理论主导文学研究时代,对于后理论时代的我们依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布鲁姆看来,是莎士比亚首开心理分析的先河,而弗洛伊德仅仅是编撰整理者……弗洛伊德在解读哈姆莱特方面并未提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哈姆莱特却对弗洛伊德的主题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依此推论,风景学、人文地理学、美学话语以及由话语繁衍出来的著述更需要文学作品或像天山这样的大地作品对其进行诠释。如果去读有关崇高美的美学原典,比如埃德蒙·伯克的《论崇高和美两种观念的起源》、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等,可能会感到晦涩难懂,然而,一旦将他们那些艰深的表述置入“天山”的语境之中,很多问题变得澄明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更熟悉的风景现实照亮(throws a new light on)了晦涩的风景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天山之于崇高美理论正如莎士比亚之于弗洛伊德。
高、李: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现实中的对象发挥想象,用语言文字(符号)对其抽象再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再现崇高天山的作品可以与崇高美理论形成互相印证呢?
张:前面我提到了洪亮吉,他是清朝中期经学家和文学家,列为“西北史地学”奠基人之一,因言获罪,流放伊犁,结果,政治厄运带给他一次寻找崇高美的壮游,成就了他的天山书写,比如《天山客话》、《天山赞》和《天山歌》。其中,《天山歌》的崇高美要素非常明显:
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
穷冬棱棱朔风裂,雪复包山没山骨。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
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
……
开首几句就勾画出天山的至高:“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至寒:“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至险:“半空石坠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而一种英雄主义豪情从“九州我昔覆险夷,五岳顶上都标题”之句磅礴而出。全诗充盈着“近似疯狂的迷狂式的惊奇感”(雪莱语)——非常巧的是,洪氏戴罪壮游天山的时期(18世纪末期),英国精英阶层也正“在通往阿尔卑斯山各条路上进行崇高美的旅行”。他们和19世纪初的雪莱、拜伦等贵族诗人“翻山越岭,人游走在生死之间”,体验“惊心动魄的雄伟”和“巨大的原始震撼”。在这个意义,并未与他们相遇的洪亮吉同样经历了搅扰人心的感官体验,也即浪漫主义诗人所说的“崇高的颤栗”。
高、李:您分析的《天山歌》,还有前面提到的“横渡天山及哈萨克风俗”,在洪吉亮和谢晓钟天山风景的书写中,不少字句指向危险、恐惧、难以进入的意义,那么,崇高性是不是与高度、险度、难度等有关?即使作为当地人的我们,虽然日日与博格达雪峰相对,但是真正能登上雪山的人屈指可数,托木尔峰、汗腾格里峰以及博格达峰基本都是留给专业登山者去挑战的。
张:非常好的问题。的确,天山崇高性与其不可亲近的高度有关——那些著名的天山雪峰,平均海拔都在7000米之上,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遥远而巨大”的景物,无法接近。我们一般根据高度把山岳分成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天山绝对是高山中的高山。
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山水诗歌的很多名山海拔并不高,例如孟浩然的岘山,李白的天姥山,前者低于100米,后者不到1000米。说到岘山,武大珞珈山似乎都比它高。当然,若按文学地理价值的估量,岘山绝对属于诗人仰止的“高山”,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文学如何升华山岳的象征高度。
高、李:您提到具有文学高度的山,不一定都高不可攀,岘山、天姥山就易于登临甚至被人类开垦利用,而像天山这样高海拔的山,由很多危险陡峭的雪峰构成,是难以驯服的自然要素,让人感到恐惧,这可能就是优美与崇高美的差别吧?
张:是的。崇高之山引起恐惧,而优美之山意味着安全。面对危险的高山,我们会产生恐惧的愉悦,巨大的感动。伯克根据情感的强度区别优美和崇高——他说:“惊惧是崇高的最高度效果,次要的效果是欣羡和崇敬”;安德鲁斯教授在《风景与西方艺术》将崇高等同于“一种无法表达的恐惧 (fear beyond expression) ”。
高、李:当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旅游文化也已经进入全民视野,现在的游山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远游”是不被鼓励的,所以在中国古代,“旅行”很多,但“旅游”的文化并不发达[4],那么您前边提到对山的迷恋审美到如今旅游文化中的游山这种变化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
张:从山之恋到游山的演化过程,段义孚和法国建筑学教授卡特琳·古特都有非常出色的论述。前者在《恋地情结》专辟一节讨论“环境态度的转变:山岳”,后者的《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刚刚在国内出版,第一章第一节“山,远处的消费场域”部分观点也许是段著的隔代回响。概言之,中西对于山岳的理解都随着时间而变化,“都是从以恐惧、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的审美情趣,再演化为近现代的观念即认为山是一种供人们休闲娱乐的资源”。[5]
高、李:您大致给我们勾画了一幅山文化发展图景,山这个客体是如何进入主体的审美视野之中,如何变成美术绘画或者文学作品的呢?
张:对于这个过程,安德鲁斯教授在他的《风景与西方艺术》做过出色的论述。总之,就是“由土地进入风景,由风景进入艺术”,具体到山,我们可以转述为“由山地进入山景,由山景进入艺术”。再具体到天山,一度拒人接近的天山成为审美对象,又再现为风景艺术——要比较完整地呈现这个过程,需要写好几本专著。我很期待更有在地优势的新大同事,也就是说作为天山风景一部分的景中人(insiders)的您们来做这方面的研究。
高、李:对于一些极远的地方,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或者不在当地生活的原因,我们对这个地方做的就是空间想象,或者去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感受这个地方,这和在那里生活的人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团队跟随邹赞教授做军垦文化研究,从沙海老兵的口中得知那个年代,那些地方的风景记忆,和来新疆到此一游的游客的记忆肯定很不一样。
张:这正是我需要了解、尚不了解的地方知识。你们的口述史对象如何从内地进入天山地区?他们的第一印象?他们面对缺氧酷寒的心理反应?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环境?兵团作家和艺术家如何描写自己逐渐熟悉的天山景物……所以说,我高度认同邹赞教授近年来完成的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工作,这项研究太有价值,必将丰富我们这些景外人(outsiders)对于天山风景以及它的崇高性的理解。
高、李:再回到崇高的山景的艺术再现这一话题。在研究吉尔吉斯坦电影风景的时候,邹赞教授要我们关注了一些周延材料,包括那些再现高山的风景画,如《雾海上的旅人》。
《雾海上的旅人》 张:弗利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雾海上的旅人》,几乎所有谈论浪漫主义风景或崇高风景的专著都会选用这幅绘画作为插图。所谓雾海,其是也是山中云海。在18世纪后期,阿尔卑斯山之所以能够演进为欧洲人寻找崇高美的目的地,风景画家功不可没。说到这里,我插一句: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第三部分专讲山之恐惧和山之审美。其中一小部分谈到中国黄山迷恋的审美传统,很有参考意义。
高、李:《雾海上的旅人》的景中人十分突出,虽然背对着观看者。(这一点,与中国山水画很不一样,我们的人物基本都隐藏在山间溪谷之中了。)他目光投射四周,凝视群山并产生某种思索。弗利德里希的这幅画创作于1818年,而早在1808年玛丽·帕拉迪斯登上了勃朗峰,成为第一位登顶的女性登山者,为何在弗利德里希那个时代高山风景画中不见女性的身影?
张:凝视群山,山也就变成了被凝视的对象。弗利德里希的凝视就是男性的凝视,或者说,帝国的凝视。无论中西,高山风景一度都是男性主导的风景。换言之,被视为崇高的风景,从雪山到沙漠到大海,很多世纪里,基本上就是男性风景,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就把崇高界定为一种性别美学。直到某一天,一位女登山者,或者女扮男装的女登山者也站在群山之巅俯瞰一切,才能改变了风景的性别。
高、李:从登山运动着手研究性别问题,这真的是为女权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对于这幅画,您是否还有新的诠释角度?
张:这幅画已从多个角度被人诠释过了,包括帝国、性别、民族、阶级等。我个人觉得,还是段义孚解读得最好,他写过一本《浪漫主义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可以为新大团队正在做的中亚电影研究提供一些侧光。他分析的浪漫主义的经典风景,如高山、沙漠、冰川等,其实也是大天山风景的构成要素。
高、李: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有浪漫主义画派、浪漫主义音乐、浪漫主义文学等,“浪漫主义地理学”的确是一个新颖的领域。浪漫主义文学由于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所产生,强调“自由取代理性成为最高价值,所有的范畴都出自人的自由心灵,一切理性规则和习惯都要用自由这一最高原则衡量一番”,诞生了拜伦、华兹华斯等文学巨人。在您看来浪漫主义的地理学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和风景之间的联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张:这个问题很大,我需要慢慢回答。其实,段义孚已经回答过了,但是如果讨论到作为浪漫主义风景的天山,我们需要新的答案。我相信,最好的答案一定会产生在新疆本地学者当中。
高、李:您耕耘在“风景与文学”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对于想要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请您推荐几本权威读书,谢谢!
张:若就山景研究,尼克尔森(Marjorie Hope Nicolson)《山之阴郁、山之光荣》(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浪漫主义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和《风景与记忆》是基础读物,其中,第一本不仅影响了段义孚,更是影响了沙玛。这三本书也可连缀成风景主题下的“山景研究”系列。
高、李:您的推荐为想要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非常感谢。
张:其实,我更期待你们的修正性回应(revisionary response)。
高、李:您今天关于“天山与崇高美”的讲解将鼓舞更多的人真正地登上高山感知这种崇高美,同时为我们进入“登山文学”、“风景文学”、“文学与艺术”甚至天山文学提供方法论的光亮,激发更多的研究者。
张:谢谢!
注释
1.邹赞、萨玛拉:《历史记忆、文化再现与风景叙事——聚焦吉尔吉斯斯坦近十年重要电影》,载《当代电影》2020年第5期,第84-90页。
2.详见谢晓钟:《新疆游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
3.高建平:《“崇高”概念的来源及其当代意义》,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第113-117页。
4.彭兆荣、邹赞:《移动的边界:论旅游文化与旅游人类学——访彭兆荣教授》,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6-12页。
5.【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5页。
《涉渡者的探索——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名家访谈录》,邹赞、朱贺琴 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访张箭飞教授:风景与文学——作为浪漫主义风景的天山》,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