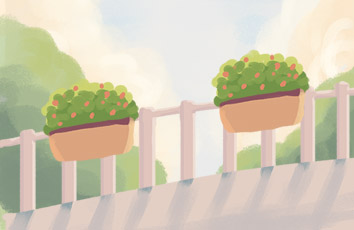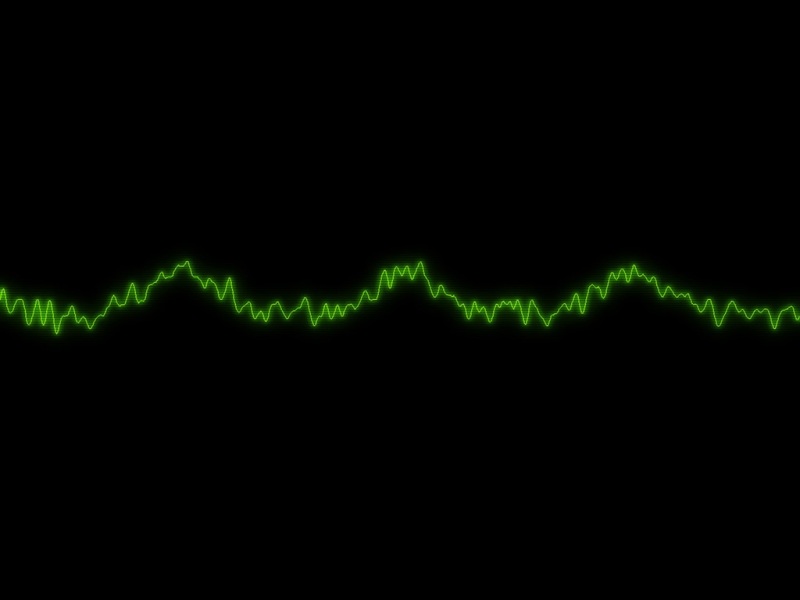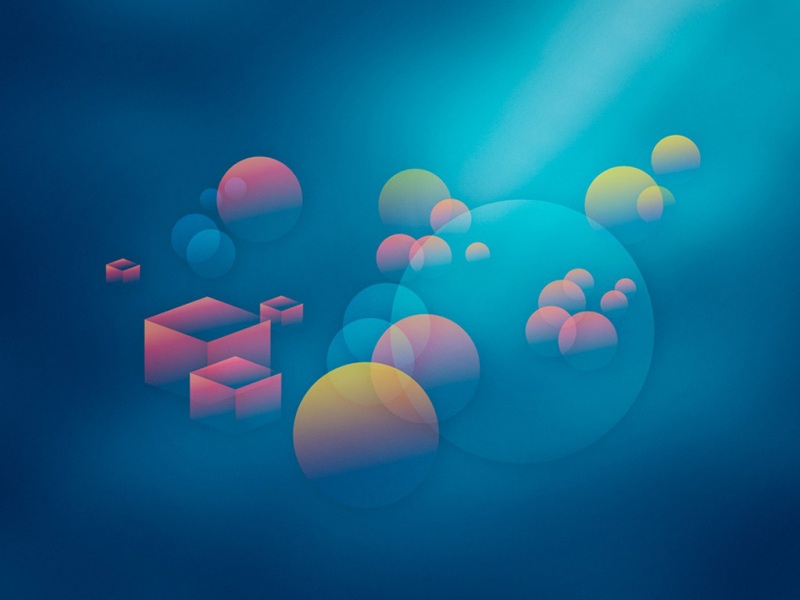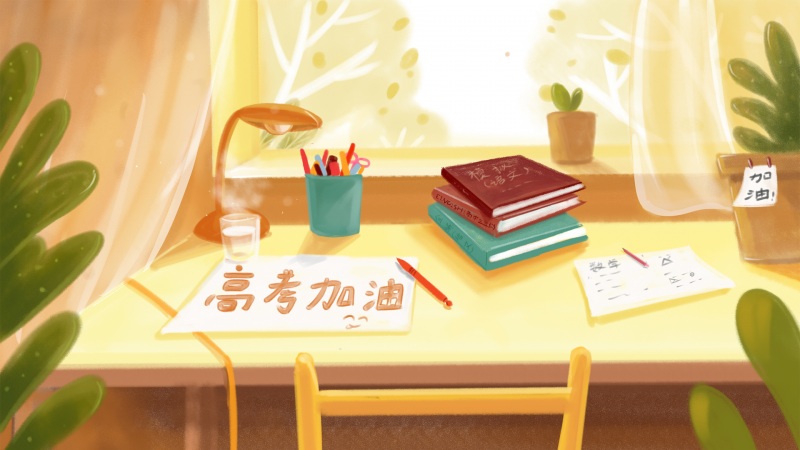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11731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4 分钟。
文ˉ董丽慧
【内容摘要】“跨文化艺术史”作为艺术史学科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主张从“形象”“影像”“重影”三个维度,追踪视觉图像中的“事物”“自我”及其“文化传统”。该研究方法致力于以“跨界”的新视野,重塑为以往艺术史叙事遮蔽的全球联动的文化传统,这方面成果尤以“跨文化文艺复兴”的艺术史个案研究为代表。而这一“跨文化”的“跨”,可从“超越”“变容”“融生”三种建设性层面加以理解。
【关键词】跨文化艺术史跨文化文艺复兴图像跨媒介艺术史方法论
2020年10月,中央美院李军教授新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问世(图1),这是继2018年“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大型学术性展览(图2)、2019年《跨文化美术史年鉴I: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以来,李军教授对其近十年来积极探索的“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系统性阐释和全面展示,也是对其2016年专著《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提出的“跨媒介艺术史”研究视角的进一步转换和持续推进。
图 1ˉ《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2020)书影
图 2ˉ“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 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览现场(2018)及图录书影
如果说2020年上半年的关键词是“疫情”和“隔离”,随着2020年下半年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严密“隔离”的防控思想逐渐让位于防护式的“共生”,人们逐渐趋于相信,也许病毒不会被彻底消灭,也许最终的“战胜”更多依靠人类抗体进化或人类科技进步而达成病毒与人类彼此和解与“共生”。从试图严密划界的“隔离”到直面不可划界的“共生”,“跨文化”的隐喻在2020年成为一种切实可感的生命体验。那么,在经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同呼吸、共命运”的2020年,在人类共同经历着以全球隔离为代价却仍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长达10个月之际,“跨文化艺术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致力于跨越文化和媒介等诸种人为区隔的边界,可以说是当前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联动的大势所趋。
一、形象、影像、重影:追踪“三重投影”的艺术史方法论
什么是“跨文化艺术史”?本书开篇即给出定义:“在艺术作品和图像中追踪事物、自我和文化之三重投影的艺术史。”[1]作为理解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提纲挈领的篇章,笔者认为,导论《从图像的重影看跨文化艺术史》突显了绘画起源的三种解释与跨文化艺术史致力于追踪的“三重投影”的对应关系。文中关于“影子”的三种叙述,可分别对应关涉西方绘画起源与发展的“影子说”“镜子说”以及作为图像传统的“重影”。
“影子说”即古罗马老普林尼讲述的绘画起源于女孩描摹情人的肖像轮廓,作为对外在客体之“形”的描摹,可对应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中“追踪事物”的维度。“镜子说”即文艺复兴阿尔伯蒂以那喀索斯沉迷于水中镜像为绘画本质,作为对自我主体之“影”的探寻,可对应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中“追踪自我”的维度。作为图像传统的“重影”则更为复杂,作者一方面将“重影”溯源自古希腊柏拉图“理念—现实(理念的影子)—艺术(现实的影子)”,即“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的断言,另一方面将“重影”溯源自古埃及“卡(灵魂)—影子(灵魂的初次显现)—图像(灵魂的替身)”,即图像作为灵魂的“重影”(double),虽然也与“灵魂”隔了三层,却并不存在柏拉图上述三层关系中视艺术为末流的等级秩序,而这两种不同的“重影”,均作为对“影子的影子”的隐喻,共同指向探寻“自我的投影又是谁的投影”这一问题的不同路径。显然,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品的“自我的投影”,均是“图像传统”这一“重影”的影子,此处的“重影”则可对应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中“追踪文化”的维度。
可以看到,“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致力于对“形象”(外在世界的投影)、“影像”(作为外在世界镜像的内在自我)、“重影”(塑造自我的图像传统)的“三重追踪”,三者可分别对应作者所说“事物、自我和文化之三重投影”[2]。而相比柏拉图式三者之间线性演进的等级关系,这“三重追踪”在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实操中,更接近古埃及(或非西方传统)三者之间在合作中互为映现的共存关系:作为事物(即“形象”)和自我投影(即“影像”)的艺术(或统称为“图像”),是有生命的图像,而他们的“重影”所对应的传统或文化,则是承载真理并使其显现的替身(double)。“图像”及其“重影”并不虚无也并非停留于完全抽象的理念层面,既不是“纯然之物”,也不是二元对立意义上“无生命的物”,而是以实体显现观念的物质性的存在,是文化传统和生命体验的物质载体。笔者认为,对“图像及其重影”三重关系的认识,是理解“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基础。
二、划界、破界、跨界:重塑“跨文化文艺复兴”
如作者所述,“跨文化艺术史”是“在艺术作品和图像中追踪事物、自我和文化之三重投影的艺术史”,也是“跨越事物、自我和文化之三重边界”的艺术史[3],而以追踪“三重投影”的方式试图实现的目标,最终还是“跨界”。这一以实现“跨界”为目的的研究,始于第一编对人类逐步进入全面“划界”时代的重申。所谓全面“划界”时代,笼统地说,指的是从黑死病结束和真正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的15世纪至20世纪落幕的500年间,这也正是人类历史全面实现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阶段。其中,主权国家的国界、个人权利的界限,以及更为晚近的“文化边界”(cultural border)等人为“划界”,均在这500年全球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逐渐成为当今人际交往和文化艺术交流的现实基础。
回顾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史,清晰可见从“划界”到不断“破界”的研究进程。虽然“文艺复兴”(Rinascita)一词肇始于16世纪“艺术史之父”瓦萨里(Giorgio Vasari)笔下,但真正使“文艺复兴”(Renaissance)“划界”成为一个时代艺术史的重要研究的,则晚近至19世纪后期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研究。而这一将“文艺复兴”仅“划界”于意大利的布克哈特式“狭义文艺复兴”,在20世纪初即经由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等学者,拓展至包括北方低地国家在内的“弗莱芒文艺复兴”(Flemish Renaissance)。进入21世纪,随着“多元文化”和“世界艺术史”研究的兴起,学界对已成经典的“文艺复兴”持续进行着地域、文化和艺术形式上的“破界”,力图囊括更广大地区和更多元文化的“伊斯兰文艺复兴”“宋代文艺复兴”等“多个文艺复兴”的研究亦相继问世(图3)。然而,“多个文艺复兴”研究却既难免使非西方文明再次成为西方视角主导的文化大餐中浮于表面的装饰拼盘,又常常事与愿违地强化了诸种文化“边界”及其潜在冲突。同时,这种试图以越来越多的“多元”持续“破界”的研究方法,虽然对于解构旧有学术观点和以新视角挖掘新史料有所助益,但除此之外,往往难以触及艺术史学科既有的更为深层的观念和内在主导逻辑,在推进艺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缺乏积极的建构性。
图 3ˉ《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中译本(2017)书影
在经历了500年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划界”、20世纪后半叶以解构主义为高潮对旧有学术体制的“破界”之后,进入21世纪,显然无视作为历史遗存的诸种“界限”或试图回到“划界”之前的“前现代(pre-modern)社会”是不现实的,而同样无视或试图抛弃作为学术史重要历程的“破界”方法,更是无法与现有学术语境对话从而积极加以推进的。那么,如何在承认既有“界限”基础上,充分利用并持续拓展以往“破界”的成果?笔者认为,应用“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重塑的“跨文化文艺复兴”,可以作为一条绕道而行的可行之路:“跨文化艺术史”并未延续正日益导向边缘研究的“破界”的方法,而是试图探究“界限”生成的深层语境和核心内驱力,以重回为后世所不断书写的“划界”的开端去颠覆“划界”的固化想象,恰恰有助于真正实现从另一个维度对学术“破界”的持续推进。
本书第一编“跨越东西:丝绸之路上的文艺复兴”的研究对象即集中于13—16世纪,此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早期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开端。第一编由三个完整个案(共七章)组成,三个个案之所以延展至七章,则是因为作者对每个个案均采用多重研究视角:从神学思想溯源“自西向东”的眺望、从实物追踪图式和观念“自东向西”的输出,还会辅之以第三重转承于“东西之间”的研究视角。第一个个案(第一、二章)是对贯穿“文艺复兴先声”(Proto-renaissance)这一西方艺术史的重要时期,“东方”作为西方神学思想之指引方向及东方建筑元素对文艺复兴可能影响的考察,始自13世纪中后期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图像,落笔于15世纪初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的“奇迹”;第二个个案(第三、四章)是对12—17世纪(主要集中在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十幅早期世界地图的细读,始自南宋《华夷图》和《禹迹图》(1136),落笔于利玛窦引进中国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第三个个案(第五至七章)则集中探讨宋元《耕织图》对14世纪锡耶纳市政厅壁画从视觉图式到理想社会观念上的影响(图4)。这三个个案亦可分别呼应现代性的开端(以中世纪晚期神学激进变革的约阿希姆主义为代表)、全球化的开端(以承载西方人对东方伊甸园由虚拟想象转为现实欲望的早期世界地图为代表)以及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跨文化的文艺复兴”的开端(深刻影响着布克哈特语义中文艺复兴早期核心地区的艺术图像与理念)。
图 4ˉ《耕织图》与锡耶纳市政厅壁画《好政府的功效》局部图像对比,以及李军教授对“丝绸”舞者的构图分析(《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第五至七章插图)
通过对这三重开端具体而微的个案考察,可以看到,13—16世纪文艺复兴的发生、现代文明“划界”和全球秩序形成了不竭的活力与动力,恰恰得益于为以往西方艺术史研究所忽视的“跨界”的文化流动。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又不仅适用于重塑一个“跨文化的文艺复兴艺术史”,李军教授新近更将这一方法应用推进至18世纪,以丰富的图像、图式和物质文化力图实证,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并非仅作为不足轻重的异域装饰,更是登堂入室影响了法国学院派绘画等级中最为重要的历史画(peinture d’histoire),而彼时正值启蒙运动这一欧洲现代文化艺术体制建构的关键节点,欧洲主流艺术和思想界亦因再次面对想象中的“东方他者”,最终促成了其现代思想观念的重要转变。[4]
三、超越、变容、融生:从“跨媒介”到“跨文化”之名
近年来,“跨媒介”和“跨文化”议题已成中文学界热点,但其代表性观点对应的内涵、文脉、语境和西文对译各有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军教授曾在《可视的艺术史》一书中尝试使用并构建“跨媒介艺术史研究”(Transmediary Perspective of Art History)方法(图5)[5],至2020年新著问世,李军教授转而提出,“鉴于媒介之间的差别和转换仍然是一种物质文化现象,故笔者现在更倾向认为,这种艺术史的新诉求(指跨媒介艺术史)属于‘跨文化艺术史’的范畴”[6] 。新著中,“跨媒介”对“跨文化”之名的从属关系,也清晰体现在第二编“跨越媒介”的标题中。不过,结合李军教授对诸艺术史个案的实例考证,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跨文化艺术史”(及其所包含的“跨媒介艺术史研究”)中,无论是对“媒介”一词,还是对“跨”的理解,都并未简单取用二者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方式,而是融合多重含义并最终以“跨文化”之名注入全新含义。笔者认为,从李军教授对“trans”一词的使用方式及其对“媒介”含义的解读出发,或可为理解和追踪“跨文化艺术史”方法论思想脉络及其深层内涵的一个入口。
图 5ˉ《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2016)书影
先看“trans”一词。“跨”的语义从强调多元共存和关系网络的“交叉”(cross-)和“之间”(inter-),到强调超越、重建、生成式的跨越(trans-),其西文对译的不同,往往直接承载着内涵和文脉的差异。而笔者注意到,从“跨媒介”到“跨文化”之名,李军教授十余年致力于推出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论虽持续拓展,并最终以“跨文化”涵盖了“跨媒介”,但其中“跨”所对应的西文始终清晰地标注为“trans-”。在阅读作者相关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至少可从“超越”“变容”“融生”三个角度解读具有多维度内涵的、作为“trans”的“跨”。
首先,就艺术史术语层面而言,作为“超”的“trans”,可类比于“超前卫”(trans-avantgarde)之名对“trans”的使用。“超前卫”,这一用于描述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新写实绘画复兴的“前卫”艺术术语,在彼时语境中,既反对为抽象表现主义所席卷的当代抽象艺术,也不同于为波普或贫穷艺术所统摄的以实物消解笔触的当代观念艺术,而是对这一系列当时盛行的艺术范式的“超越”。其实现形式则是回归文艺复兴以来扎根意大利本土的绘画传统,同时不放弃在绘画观念层面呈现基于传统神学和现代心理学的深层思考。因而,在艺术史术语层面上,这一“超越”并非线性意义上的“超过”或“越过”,正如同意大利“超前卫”既不同于“新前卫”(即字面上的“超过历史前卫”)也不同于“后前卫”(即字面上的“越过前卫之后”),而是对现行艺术史范式或“融通”、或“生成”式的重新建构,其实现形式则往往有赖于重塑被遗失的传统。
其次,就艺术理论术语层面而言,作为“变”的“trans”,可类比从神学到美学意义上的“变容”(Transfiguration)或“嬗变”(transfiguration)一词前缀。李军教授曾借由这一词语,追溯了丹托(Arthur Danto)对于寻常物和现成品艺术区分法则的神学思想脉络(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A Philosophy of Art, 1983),从“(耶稣)变容”(图6)这一基督教术语到“(寻常物)嬗变”这一当代艺术理论术语,寻常物成为现成品艺术,正如同耶稣变容,“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新约·路加福音》9:29)[7]。然而,在实现从寻常物(可对应耶稣人性)到艺术品(可对应耶稣神性)的升华过程中,李军教授指出丹托的问题所在:“丹托在正确地引用基督教观念‘trans-figuration’,以表述艺术经验中‘平凡的变容’的同时,却丢掉了其中的精髓——同样作为一种真实的视觉经验的‘变容’本身。”[8]因而,在艺术理论术语层面上,这一“超越”并非仅从神学理念到美学理论的纯粹观念演进,而是强调着眼于“真实的视觉经验”,却又不仅停留于物质性的、形而下层面的感官本身,而视这一“视觉经验”为承载着文化传统和观念演进的媒介。
图6ˉ耶稣变容 ˉ木板油画 ˉ405cm×278cm ˉ 拉斐尔 ˉ1518-1520年 ˉ 梵蒂冈博物馆藏
最后,回到“跨文化”或“跨文化性”作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热议的跨学科术语本身,“trans”的语义则更多指向“融生”。一般认为,“跨文化” (transculturation)一词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始自人类学研究,由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在20世纪40年代最早使用,用于研究殖民地在被迫种植和生产烟草和糖的殖民化进程中,同时基于混杂着本地传统和外来经验的本土现实,而自然生发出的新的文化形态。[9]与这一“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相对的,是“文化消亡”(deculturation)和强调趋同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这一传统二分法的研究模式。更进一步,“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一词则在20世纪末,随欧洲移民和种族问题激化的现实语境,在学界逐渐成为重要议题,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对这一“新的文化观念”阐述如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阐述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跨文化特性观念(transculturality)。这种观念的基本意思是旧的国家文化观念已经过时,‘文化’不再被国家之间的界限所限制,现在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这种身份认同不再是核心结构,而是枝状结构或网状结构,它们远远超越了传统文化和国家文化虚构的边界,整合了本地、国家和全世界的元素,简而言之,它们是跨文化的。[10]
2017年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中,韦尔施做了这次名为《历史上的跨文化特性》的发言,从跨地域(包括从古希腊与近东之间、近现代欧洲内部之间、当代全球移民间的跨文化交流)、跨时代、跨不同艺术媒介(包括建筑、音乐、舞蹈、绘画、民艺等艺术门类)多个维度概括性地描述了“跨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曾发挥的作用,认为“跨文化特性”是“历史的规律”,不仅于此,“跨文化特性不是某种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而是与我们共存的、使我们成为我们的东西”。[11]
虽然在韦尔施等理论家的呼吁下,“跨文化”研究理论逐渐在学界流行,但如果缺乏持续而深入的实例支持,则要么成为理想主义的口号,要么仅止于现象表面,要么仍以“多元”的名义维护着作为惯例的文化壁垒,因而这一术语也被指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12]。正是在综合了上述艺术史术语层面的“超越”和艺术理论术语层面的“变容”、结合实证与观念、物质媒介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充分认识并有效融合现有边界的基础上,在破译寄托于多重镜像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最终指向“融生”这一具有建设性和自由活力的“生命”特质。
再看“媒介”(medium)一词。可以看到,李军教授近十年从“跨媒介”到“跨文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推进,一方面一以贯之的是对“媒介”含义狭义和广义的双重融合,另一方面也可见出其新著对广义“跨媒介”的推进。狭义和广义媒介均可定义为“艺术作品的物质载体”[13],但狭义媒介一般仅就艺术品本身的物质层面而言,分类依据一般依托于不同物质材料、不同技艺分科和不同呈现载体的媒材,可称之为“艺术门类”,这体现在艺术史个案研究中对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绘画、建筑、雕塑、摄影等媒介彼此之间既相互影响又彼此不同的门类特质的关注。在艺术史研究中,对这一狭义媒介区隔的充分把握,有助于时刻警醒研究者:媒介既非透明,也常常并不对等,而是各有媒介特性。在《跨文化的艺术史》中,这首先体现在第二编以“媒介竞争”指称的“诗与画的竞争”中。尤其在第二编第一个个案对《后赤壁赋图》的诗画研究中(第八章),作者通过对画卷前段“图文对应”和后段突现“图文不对应”的细读,不仅为古画断代提供了有力的图像证据,更深入到对图像背后“藏意”的探究(图7)。
图 7ˉ 乔仲常(传)《后赤壁赋图》局部:正面表现的临皋亭苏轼与二客及影子(《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第八章插图)
不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跨文化艺术史”对“媒介”含义的使用不止于狭义的“艺术门类”,而是致力于探索更为潜在的使用方式。这一潜在更广义的“媒介”首先包含着“文化形式”的层次,即用于指称呈现艺术品整体(包括质料、观念、传统、时代和时间性在内)及为其提供展示氛围的物质性载体,这显著体现在《可视的艺术史》中对“教堂、博物馆、艺术史、关于艺术史的图像”这四种“文化形式”(或媒介)的分类上。正是在此分类基础上,《可视的艺术史》完成了对西方艺术史从前现代教堂到现代博物馆展示场域演进、从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艺术史体制的建构到当代艺术终结论的观念追溯。
如果说按照“艺术门类”划分的狭义媒介是现行艺术体制和学术研究的惯例,按照“文化形式”划分的广义媒介,则是从观念建构成形的历时性层面对现行惯例进行深入溯源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而这个步骤在《可视的艺术史》中已架构完成。那么,就对广义“跨媒介”研究方法的推进而言,新著推出的“跨文化艺术史”不仅关注延续自西方现代脉络的、作为“文化形式”的艺术媒介,更进一步将对“跨媒介”的理解拓展至融通情感和艺术家生命的层面,这明显体现在第二编的后两个个案中。
第一个个案是关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诗情与生死纠葛对林、梁建筑思想转向的影响。作者认为,1931年徐的罹难,促成了林将中国传统建筑结构上升至哲学和伦理学高度(以中国古建木结构既是“骨架”、本身也是建筑装饰这一“内外一致性”,比附“诚实袒露”的人格精神),并深刻影响了梁思成在1932年发生的从“古典折衷主义”到“结构理性主义”建筑风格的转向(第九、十章)。
第二个个案是对沈从文作为文学家(1924—1934)、艺术家(1934—1949年“图像转向”)、学人(1949年自戕未遂之后投入物质文化研究)三个生命阶段“转业”之谜的解读。作者认为,这一系列看似突然的“断裂”,与沈的婚恋、情感、理想等人生阅历和家国情怀有着“内在的连续性”。比如,其中“图像转向”阶段,“彩色画”的开始与中断,实际上伴随着此间一段婚外恋情(“新的欲求对象”)的出现和结束;而1957年家书中的速写亦非简化的“左右”政见对峙,乃是源自其五一节从窗口向下俯视众生、对“上下”等级结构颠覆的愿望,究其根本是对底层劳动者的认同——而这源自他早年生活经历的认同,亦可解释为他在人生第三阶段发生物质文化研究转向的一个具有延续性的内在动因(第十一、十二章,图8)。
图 8ˉ 沈从文《从住处楼上望下去》(1957)与夏加尔《透过窗户所见的巴黎》(1913)(《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第十一章插图)
综上可见,如果说狭义媒介主要指承载艺术品质料的现行“艺术门类”,广义媒介主要指系统性书写和架构现代艺术演进的、可视的“文化形式”,上述两个个案则将“媒介”的含义扩延至研究者本身(即狭义媒介和广义媒介的承载者)。至此,“媒介”已从研究客体拓展至研究主体,从物化的“艺术门类”和具有物质性的“文化形式”,幻化为研究者主体和“生命形式”本身。
四、有机的艺术史:文化边界之后的生命观照及方法论界限
李军教授在2008年对《庵上坊》一书所作的书评中认为它应当是从基于实证的具体精研中见微言大义,是“有限的总体艺术史”:所谓“有限”,是指其物质性,艺术史“在根本上要受到实物的限制,要仅仅满足于成为实物的注解”;所谓“总体史”,是指其微言大义的观念性,即“一件物质形态的艺术作品的生产、流通和传承必然涉及人类同时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践的全部领域(从材料、工具、工艺到观念、宗教与信仰,从政治、经济到文化)”[14]。“跨文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延续了这一“有限的总体艺术史”对实证及其潜在观念(“图像及其重影”)的双重强调,对已成范式的现代艺术体制和现代艺术史书写模式保持警惕。那么,既然不以建构抽象的宏大叙事为目标,又如何理解“跨文化艺术史”在追踪重影、跨界、融生等方面体现出的建构性特征?
笔者认为,因“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方法视以往彼此割裂的中西方文化和艺术为有机整体、视拓展至研究者主体的“媒介”为有机的研究整体,尤其是结合2020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近现实,笔者称这一新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为21世纪“后全球化时代”的“有机的艺术史”。所谓“有机”(organic),主要指以生命生成逻辑作为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将全球化以来的诸种文化艺术视为一个总体生命体,无论东方、西方,还是近年来提出的“全球南方”、北方,不同文明如同这个人类总体文化生命体的诸种细胞和器官组织,彼此联动,休戚与共。
类似于今天病毒附着于人类、弥散在空气中这一最为切近的隐喻,回顾近500年全球化进程,携带诸种文化基因的不同艺术样态,也在有形无形中彼此附着与弥散,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经历着或多或少的融合共生,或有形如外在的皮肉触碰,或无形如内部的筋骨相连,或如更消弭于无形的血脉与气息贯通。在2020年的全球疫情中,回望500多年前的全球疫情,如果说,那场以黑死病或鼠疫开启的从文艺复兴至今的全球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现代化确立的种种学科范式和“边界”的全球化,那么,从2020年新冠肺炎重新导致全球“隔离”来看,可以说,经历了500年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诸种“划界”和“破界”,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称之为“文化边界之后”的时代,一个跨界、融生的一体化时代,一个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彼此联动、无可分割,而500年全球文化艺术叙事的旧有范式亟待重新审视的新时代。
正是基于将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追因于现代社会进程中“文化边界”的反思,学者赵汀阳提出“跨文化聚点”(trans-cultural focal point)研究。从积极的方面看,他将“跨文化”(trans-cultural)视为一种能够使多种文化合力生成“新文化”的“建构性愿景”,从而区别于主要用于描述和研究现有文化关系的“文化间”(intercultural)和“交叉文化”(cross-cultural)概念[15];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赵汀阳则指出这一概念“无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认为较为容易作为跨文化兼容点的“美食、旅游、娱乐以及艺术之类”往往“缺乏重要价值,无足轻重……不足以建立信念或思想上的同心”,“文明的深层语法在于信仰、哲学、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正是这些深层语法的差异构成了难以逾越的文化边界”,因此提出“跨文化的难题不仅在于缺乏落实在文明深层语法上的跨文化聚点,而更为困难的是,还存在难以互相妥协的冲突点。对此,显然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论”[16]。而实际上, 可以看到,以“跨文化文艺复兴”为代表的“跨文化艺术史”研究,正通过对“划界”时代诸种或隐或显、或潜在或变体的“跨界”文化交流的事实性考证,既能展示出深入探究“信仰、哲学、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文明的深层语法”的潜力,又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能够以图像和物质文化实证调和“难以互相妥协的冲突点”,从而将“跨文化聚点”这一“建构性愿景”落实为兼及人类文明深层语法与普适性的实例。
如果说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19世纪,由欧洲海外殖民所拓展至全球的现代“划界”成为势不可当的全球现实,此后,经历了20世纪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及此后二元对抗的“冷战”,至20世纪后期,无论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一度甚嚣尘上,还是艺术与日常生活、艺术与非艺术、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间的诸种破界,其诉求已成为西方当代文化和艺术潜在的主导力量。丹托曾在1995年的梅隆讲座中,借用黑格尔“历史的边界之外”,提出“艺术的终结”一部分含义即在于对“边界”(pale)或划界的“墙”[包括长城、柏林墙、爱尔兰限制区(the Irish Pale)]的超越。丹托所指艺术的“边界”,在这一演讲的具体语境里,指的是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以来盛期现代主义媒介纯化的宏大叙事架构,诸如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这样因“写实”的艺术语言而被划定为“不纯粹”的艺术形态被排斥在当代艺术之外。在这里,“艺术的终结”反对的实际上是格林伯格式的现代主义艺术对其“边界”的维护,而丹托所说的“艺术终结”,实为“破界”可能性的终结,丹托畅想的“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则是“历史的边界之后”的、艺术家不再受到限制的“自由艺术”[17]。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艺术史”对艺术和生命自主性追求的主张,也同样是基于“边界之后”的当代价值重建,正如作者所说:“‘越界’其实是人类世界中一切人和事物的自主性要求,也是一切艺术和生命之自主性存在的证明。因为艺术与人的生命一样,都是自由的;而自由的,即跨越边界的。”[18]
最后,作为一种“文化边界之后”的新的艺术史方法论,“跨文化艺术史”在实际研究中是否应当设置使用界限?尤其是将其拓展至生命观照等极具主观性的层面时,如何以生命体验确证视觉文本,如何平衡“直觉”和“个人视角”在学术研究中的可信性,如何把握学术写作中投射情感与玄思的尺度?笔者对此存疑且保持警惕,恰如作者建设性地指出埃尔斯纳(Jas Elsner)和王德威教授各自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时提出的问题:“图像和文本之间存在着无数的关联和不关联的因素,是什么保证了论者是正当的?”[19]“当这种基于敏锐与善感的素质被不当地夸大,上升为一种统摄一切的方法论时,尤其是当这种方法论罔顾视觉经验和历史证据的双重制约时,上述‘睿见’必将同时转化为‘不见’,从而坠入历史谬误的深渊。”[20]也恰如作者所说,“故事总是可以有另一种讲法”[21],“一个人在井口看了一眼,看见了自己的脸”[22],现阶段,或许我们需要的恰是基于作者所强调的“三原原则”(回到原文、原作、原文化语境)、基于“大胆猜想”和“小心求证”而讲述更多的故事、看到更多的脸。笔者认为,《跨文化的艺术史》做到了,让读者看到一个个不一样的故事、一张张不同却同样充满生命力的脸。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评《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